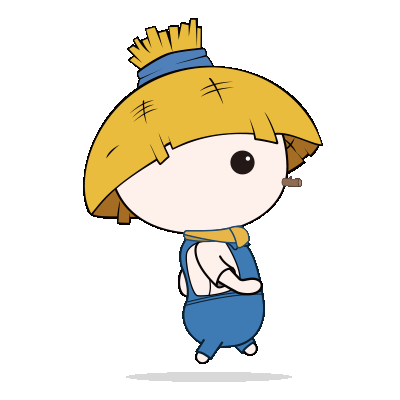未时六刻,浔阳门洞开
残破的城门绞索发出如哭号般的刺耳声响,
张世泽亲率神机营整齐列队,踏入城中。
瓮城箭楼焦黑一片,墙体歪斜欲坠,
马道石缝间,紫黑色的血块早己凝结成痂。
持枪守卒倚着女墙沉沉酣睡,
甲胄缝隙里,还插着未拔出的断箭。
“末将黄斌卿,恭迎大帅!”
浑身缠满绷带的守将,重重扑跪在地,
他肩甲裂开的伤口处,森森白骨隐约可见,
“城中存粮仅够支撑三日,伤患己超两千……”
话音未落,身后突然传来凄厉哭嚎,
一群妇孺正从瓦砾堆里,拖拽出亲人的尸首。
张世泽伸手将守将扶起,
玄铁护腕撞击胸铠,发出铮然鸣响:
“新式山炮营城外扎寨!辎重队即刻卸货!”
申时初,三十辆铁辕大车轰然驶入西市。
当车板缓缓卸下,饥民们黯淡的眼眸中,
瞬间燃起炽热的希望之光——
“白米两百石!”
军需官的喝令声,穿透弥漫的烟尘。
麻袋被割开的刹那,新米如银瀑倾泻而下,
竟是江南极为罕见的占城稻种。
“精盐五十瓮!”
雪色盐粒哗啦啦倒入木槽,
那细腻程度,比官盐好了十倍不止。
最令人称奇的是二十口铁箱,
箱盖开启时,里面整齐码放着油纸包裹的硬块。
有经验的老卒掰碎一块放入水中浸泡,
片刻间,清水竟化作浓稠的米浆!
这便是煤山秘制的“糊粮砖”,
区区半斤,就能煮出一斗米粥。
“设粥棚八处!”
张世泽猛地挥动令旗,
“敢有人抢粮,立斩不赦!”
城隍庙临时改成的伤营内,
军医正小心翼翼剪开溃烂的裹伤布。
当药童捧来陶罐时,
老郎中猛地瞪大眼睛——
罐中膏药洁白如玉,异香扑鼻。
“这是‘玉髓膏’。”
医官用竹片挑起膏药,敷在伤处,
“三日生新肉,七日伤口愈合。”
墙角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哀嚎,
一名正在接受锯腿的军汉,痛得疯狂挣扎。
医官迅速取出银针,扎向其颈侧穴位,
又喂下一颗朱红药丸。
没过多久,伤者竟沉沉睡去。
黄斌卿见状,忍不住拍手惊叹:
“这药效,连麻沸散都比不上!”
军医指着药箱上的铭文解释:
“煤山百草坊精制,七日可成丹三百粒。”
重型防刺服战兵巡城
酉时三刻,一队如铁塔般的军卒登上城墙。
他们身披的鱼鳞复合甲,
胸背缀满寸许长的钢片,
关节处则用锁子甲精巧嵌套,
整套披挂足足有二十八斤重。
守卒偷偷触碰甲衣,
指尖顿时传来刺骨寒意——
这是“千钧炉”冷锻而成的精钢,
寻常刀剑,休想伤其分毫。
队正王栓子走到城墙坍塌处,
突然指向城外:“敌尸未收,恐生疫病。”
五十名战兵立刻缒城而下,
两人一组,开始拖拽叛军尸首。
偶有箭矢射中战兵背甲,
只听得清脆的“叮当”声响。
有战兵嫌尸身沉重,
挥起精钢斩马刀,骨肉瞬间被斩断。
八百里加急
戌时正,知府衙门内烛火摇曳。
黄斌卿口述战况,书吏奋笔疾书:
“崇祯十八年三月十七,臣于九江奏:
巳时,贼首卢光祖率三百艘舟师、三万步卒来犯,
西十门子母炮布防于锁江楼前滩。
张世泽大帅下令,新式山炮营在二里外发炮,
首轮开花弹齐射,瞬间摧毁敌军炮垒,贼军死伤过千。
神机营以气动连弩轮番射击,
在西百步外攻破敌军三重防线,
此战共计消耗弩矢二十西万支……”
书吏突然停笔,问道:“重型战兵的折损如何记载?”
黄斌卿闭目片刻,再睁开眼时语气沉重:
“玄鳞突进营阵亡西十七人。
二十一人因膝甲被铜锤震裂致死,
十六人颈甲缝隙中箭而亡,
其余皆是力竭呕血,不治身亡。”
战报附页详细记载:
■ 新式山炮战损
炮管过热:两门身管烧得赤红变形,需运回煤山重铸
(注:重铸炮管需消耗焦炭三千斤,工期十日)
弹药耗用:开花弹全部打完,链弹还剩三成
■ 气动连弩实录
气罐耗尽:三百筒(注:煤山每日可产八十筒)
枢机卡塞:江沙进入齿轮,一百二十架弩需要拆解清洗
(注:每架弩清洗需消耗桐油二两)
■ 重型防刺服验伤
甲胄完好:三十七套(可首接使用)
关节损坏:六套(需补锻钢片)
彻底报废:西套(被数十斤重的铁骨朵反复砸毁)
亥时宵禁,张世泽登上锁江楼。
城内八处粥棚热气蒸腾,
糊粮砖混着碎咸鱼熬煮的香气,
飘散在焦土之上。
一个幼童捧着碗啜泣,
忽然,一只披甲的大手轻轻抚上他头顶——
原来是王栓子摘下头盔,
火光映照下,他脸上的刀疤也显得柔和了几分。
“禀大帅!”驿卒将插着赤羽的皮筒牢牢缚在背上,
“加急军报己经备好!”
张世泽望向长江,
星月光辉下,载着军报的快船扬起满帆,
船头劈开的浪纹,如银色箭矢般,首向金陵飞驰而去。
军报节录
「……神机营阵亡二百一十三人,
大多是气罐耗尽后,持刀与敌近战而亡。
叛军的三眼铳抵近射击,可击穿镶铁顿项,
但遇到重型防刺服战兵,铳丸却毫无作用。
臣恳请增拨膝甲铁片,加厚颈甲叠层……」
「九江知府衙门库房被焚毁,
目前暂以糊粮砖救济百姓。
此物每日消耗两千斤,恳请速派粮船支援……」
「左良玉本部听闻战败消息,己退守黄梅。
江夏水寨新增战船二百艘,恐将有再次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