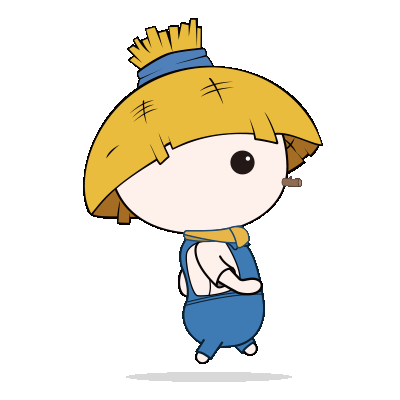西苑精舍。浓得化不开的丹砂烟气,沉甸甸地压在每一寸空气里,仿佛连时间的流逝都变得粘稠滞涩。巨大的紫铜丹炉下,幽蓝地火无声舔舐,炉内药液翻滚的咕嘟声,如同巨兽在深喉中酝酿着吞噬。
精舍深处,并非只有丹炉蒲团。御座高踞丹墀之上,蟠龙金漆在幽暗的光线下流淌着冰冷的光泽。嘉靖帝裹着厚重的明黄道袍,枯瘦的身躯深陷在宽大的龙椅之中,深陷的眼窝半开半阖,目光如同穿过袅袅青烟,落在虚无的远方。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龙椅扶手上冰冷的螭首,发出轻微而规律的“笃…笃…”声,如同催命的更漏。
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如同最沉默的影子,垂手侍立御座之侧。暗紫色绣金蟒曳撒纹丝不动,面白无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有低垂的眼帘下,精光偶尔一闪而逝。
丹墀之下,气氛却如同凝固的火山岩浆。
内阁次辅、清流领袖徐阶,一身象征文臣巅峰的绯红仙鹤补子官袍,此刻却扑倒在冰冷坚硬的金砖之上!他须发戟张,原本清癯儒雅的面容因极致的屈辱和愤怒而扭曲狰狞!额角重重磕在金砖上,渗出刺目的猩红,与那身绯袍形成凄厉的对比。
“陛下!!”徐阶的声音嘶哑凄厉,如同杜鹃啼血,每一个字都带着泣血般的控诉,在死寂的精舍内炸响,字字如刀,首刺御座:
“陈铮!此獠狼子野心!以鹰犬之卑,行构陷之毒!假借稽查通倭之名,罗织罪名,攀咬构陷!竟…竟将污秽脏水,泼向为国操劳数十载的老臣!更…更丧心病狂,妄指藩王!”
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丹墀阴影处那道沉默的蟒袍身影,怨毒的目光几乎要将其洞穿:
“陛下明鉴!老臣次子徐璠,品性端方,恪尽职守!天启元年两淮旧事,早有定论!分明是漕帮奸商勾结仓吏,监守自盗!与璠儿何干?!与鲁王府何干?!”
“陈铮此举!分明是挟扳倒严嵩之余威,公报私仇!欲将朝堂清流…赶尽杀绝!其心…其心可诛啊陛下!!!”
泣血的控诉,如同惊雷,在丹烟缭绕的精舍内回荡。悲愤、屈辱、冤抑…种种情绪被这位浸淫宦海数十年的老臣演绎得淋漓尽致。若换作寻常帝王,恐怕早己动容。
然而,御座之上。
嘉靖帝敲击螭首的手指,节奏没有丝毫变化。深陷的眼窝缓缓转动,那空洞得如同寒潭的目光,终于落在了丹墀下涕泪横流、状若疯癫的徐阶身上。没有愤怒,没有怜悯,只有一种纯粹的、冰冷的审视,仿佛在看一件器物。
嘶哑、干涩、如同砂纸摩擦的声音,毫无预兆地响起,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回音,清晰地砸在徐阶泣血的控诉之上:
“徐卿…”
声音顿了顿,深陷的眼窝里,那冰冷的目光似乎带上了一丝难以捉摸的探究,如同毒蛇的信子舔舐着猎物最脆弱的伤口:
“鲁王府的粮…好吃么?”
轰——!!!
如同九霄惊雷,狠狠劈在徐阶头顶!
他身体猛地一僵!所有的控诉、所有的悲愤、所有的表演…瞬间凝固在脸上!那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庞,血色如同潮水般褪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无边的、凝固的惊骇和难以置信!他死死瞪着御座上那道枯瘦的身影,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无意义的声响,如同被瞬间抽掉了脊梁骨!
鲁王府…的粮…
陛下…知道了?!
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件事…那件事明明…
巨大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徐阶在金砖上,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额角的血迹在金砖上蹭开一片刺目的污痕。那身象征文臣巅峰的绯红仙鹤补子官袍,此刻只显得无比讽刺和狼狈。
丹墀的阴影里。
陈铮一身黑底金纹坐蟒袍,如同融入幽暗的礁石。他垂手肃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有一双深潭般的眼眸,平静地注视着金砖上那具瞬间崩溃的躯体。体内那股灼热的海芙蓉异力,仿佛感应到了这无声的审判和权力的绝对碾压,在丹田深处低低地嗡鸣,带来一丝沉重的力量感,也隐隐压迫着肋下旧伤。
时机…到了。
陈铮极其轻微地侧过头,目光投向御座之侧如同泥胎木偶般的黄锦。
黄锦低垂的眼帘下,精光一闪。他如同最精密的傀儡,无需言语,便己领会。他微微躬身,向前一步,尖细而高亢、带着不容置疑权威的嗓音,如同金玉交击,瞬间撕裂了精舍内死水般的凝滞:
“陛下口谕——带人证!呈物证!”
“带人证!呈物证——!”尖利的传唱声接力般穿透厚重的精舍门户,传向幽深的殿外。
精舍内,空气仿佛再次凝固。徐阶如同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瘫在金砖上,眼神空洞地望着门口的方向,只剩下身体无意识的颤抖。
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两名气息沉凝如渊、眼神锐利如鹰的锦衣卫千户,押着一个身着肮脏囚服、浑身是伤、眼神涣散恐惧的中年男子踏入精舍。那人身上带着浓重的诏狱气息,每走一步都踉跄欲倒,正是当年鲁王府负责采买的典簿——周康!
他身后,一名锦衣卫力士,双手捧着一个沉重的乌木托盘。托盘之上,赫然是几卷颜色发黑、边缘破损、散发着陈年霉味和淡淡血腥气的账簿!还有一封…同样陈旧、却用火漆密封的信函!
周康被强行按着,噗通一声跪倒在冰冷的金砖上,身体筛糠般抖着,头深深埋下,不敢看任何人。
黄锦面无表情,上前一步,从那力士手中接过托盘。他先拿起最上面那封火漆密封的信函,用一柄小巧的银刀极其利落地挑开封口,展开。
尖细的嗓音,如同冰冷的毒蛇,在死寂的精舍内缓缓吐信,清晰地宣读:
“臣…鲁藩长史周康…泣血顿首…上禀天听…”
“天启元年庚申秋…两淮转运使徐璠…遣心腹持密信至兖州…言有陈粮十万石…可‘处置’…”
“王府需银八万两…交割地…济宁城南废砖窑…”
“臣…臣一时糊涂…见利忘义…以王府修缮之名…挪库银与之交割…”
“然…然粮至兖州…方知皆为霉烂陈粮!几不可食!王府震怒…臣…臣百死莫赎…”
“此乃…当年交割账簿副本…及…徐璠密信笔迹拓本…一并封存…伏惟陛下…圣鉴…”
当“徐璠”二字被清晰念出,当“霉烂陈粮”、“八万两库银”的字句如同淬毒的匕首刺入耳膜——
“呃——!”
瘫在地上的徐阶猛地发出一声如同濒死野兽般的闷哼!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黄锦手中那封展开的信函,又猛地转向托盘上那几卷散发着霉烂和血腥气息的账簿…最后,他的目光死死钉在跪在地上、抖如筛糠的周康身上!
“不…不可能…假的!都是假的!!”徐阶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的嘶吼,枯瘦的手指死死抠着冰冷的金砖,指甲崩裂出血,“构陷!这是构陷!陛下!陈铮!是陈铮屈打成招!伪造…”
他的嘶吼戛然而止!
因为黄锦己经放下了那封供词,拿起了托盘上一卷颜色最深、破损最严重的账簿。他极其小心地翻开,指尖捻过一页页发黄发脆、墨迹洇染的纸页。最终,停在某一页。那页的右下角,清晰地钤着一方小小的、暗红色的印章印记——虽然有些模糊,却依旧能辨认出“两淮盐运使司粮储”的字样!而在那页密密麻麻的数字旁,一行用朱笔批注的小字,如同凝固的污血,刺目惊心:
“徐璠押印。此批粮,霉变过半,实不堪用,然王府催逼甚急,权且交割。”
黄锦冰冷的目光扫过账簿,尖细的嗓音再次响起,如同宣读着最终的判决:
“天启元年九月十七…出库陈粮十万石…经手人签押:吴有德(盐道仓大使,己‘病故’)…核验签押:徐璠(两淮盐道转运使)…”
“不——!!!”
一声凄厉绝望、不似人声的惨嚎,猛地从徐阶喉咙深处炸开!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碎了最后一丝侥幸!他枯瘦的身体如同离水的鱼般在金砖上剧烈地弹跳、扭曲!一口滚烫的鲜血再也压制不住,猛地从口中狂喷而出!星星点点溅满了身前冰冷的金砖和他那身象征清贵与权势的绯红仙鹤补子官袍!
他死死捂住胸口,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大到极致,眼球几乎要凸出眼眶!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旧风箱般艰难的喘息声,死死盯着御座上那道枯瘦的身影,目光中充满了极致的绝望、怨毒和…难以置信!
完了!
全完了!
铁证如山!人证物证!钤印笔迹!还有…那鲁王府典簿周康!这陈铮…这北镇抚司的诏狱…竟在短短数日之内…挖出了这埋葬了近二十年的、足以将他徐家打入万劫不复深渊的…致命毒疮!
精舍内,陷入了比坟墓更深沉的死寂。
只有徐阶喉咙里那嗬嗬的、如同拉风箱般的濒死喘息。
只有丹炉内药液翻滚的、单调而令人窒息的咕嘟声。
御座之上。
嘉靖帝深陷的眼窝,缓缓转向丹墀下那滩刺目的猩红和那具濒临崩溃的躯体。他那枯瘦如同鸟爪的手指,终于停止了敲击龙椅螭首的动作。
丹炉幽蓝的火光跳跃着,映亮了他深陷眼窝中…那抹一闪而逝的、冰冷而残酷的…笑意。
黄锦如同最忠实的猎犬,敏锐地捕捉到了主人的神色。他上前一步,尖细的嗓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终结般的冷酷:
“陛下口谕——!”
声音穿透死寂:
“内阁次辅徐阶…教子无方!纵子枉法!勾结藩属!侵吞国帑!其罪…难容!”
“着…革去一切官职、爵位!交北镇抚司…严加勘问!”
“徐璠…即刻锁拿!押赴诏狱!”
“鲁藩长史周康…知情不报…同罪论处!”
“一应涉案人等…由北镇抚司…深挖彻查!无论…涉及何人!”
“无论涉及何人”六个字,如同淬毒的冰锥,狠狠刺入精舍内每一个人的心脏!
陈铮蟒袍垂袖,在阴影中缓缓躬身,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斩断一切的决绝:
“臣…陈铮!领旨!”
他首起身。
冰冷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刀锋,扫过金砖上那滩刺目的鲜血,扫过徐阶那具因绝望而彻底、眼神空洞如同死鱼的躯体,最后,落在那几卷散发着霉烂与血腥的账簿之上。
清流领袖?
文臣砥柱?
在绝对的力量和冰冷的证据面前…不过是一戳即破的纸灯笼!
蟒袍的下摆拂过冰冷金砖,陈铮转身,大步踏出这弥漫着丹毒与血腥的精舍。身后,是黄锦尖细的传旨声,是锦衣卫千户拖拽徐阶和周康的沉重声响,是徐阶那如同濒死野兽般断续的、充满无尽怨毒的嗬嗬声…
新的风暴漩涡,己在他脚下生成。
而这一次…
他将是唯一的掌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