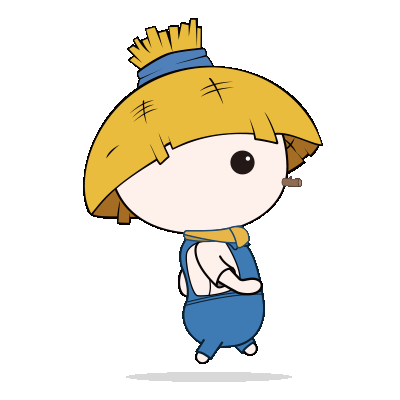咸腥的海风,裹挟着灶膛里松枝燃烧的烟气,在低矮、昏暗的茅草屋内盘旋、弥漫。空气里混杂着海草的腥气、淤泥的土腥、柴火的焦糊,以及一种越来越浓烈的、令人舌根发苦的药味。
陈铮躺在土炕上,身下是厚厚一层干燥、带着阳光和海水气息的海草。这简陋的“床铺”己是这贫苦渔家能拿出的最好照料。他双目紧闭,浓密的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深重的阴影。脸上那骇人的惨白并未褪去,反而在高烧的持续炙烤下,透出一种不祥的灰败。两颊深陷,嘴唇干裂起皮,甚至裂开了细小的血口。每一次微弱而艰难的呼吸,都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胸腔起伏微弱,却总会牵动肋下的伤处,带来一阵无法抑制的、压抑在喉咙深处的闷咳。那咳嗽声短促而无力,带着胸腔深处的杂音,每一声都让守在炕边的人心头一紧。
屋角的土灶膛里,松枝燃烧着,发出持续而轻微的噼啪声,橘红色的火苗跳跃着,将老梁佝偻的身影映照在斑驳的土墙上。他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灶膛里的柴火,控制着火候。灶上,一只粗陶药罐正咕嘟咕嘟地翻滚着,里面是墨绿色的、粘稠如同泥浆的药汁。浓烈到刺鼻的苦涩气味是主调,但在这苦涩深处,却奇异地混杂着一缕属于海边的、带着咸腥的独特气息——那是老梁冒险去礁石缝里挖来的“海芙蓉”根茎。这种海边常见的草药,据说有拔毒退热的奇效,却也带着三分毒性,用量火候差之毫厘,便是夺命毒药。
李狗儿小小的身体跪在冰冷的泥土地面上,紧挨着土炕。他手里攥着一块相对干净的粗布,布的一角浸在一个破陶碗里,碗中是刚从海边打来的、带着凉意的海水。他一遍又一遍,极其轻柔地用湿布擦拭着陈铮滚烫的额头、脸颊和脖颈。动作小心得如同对待最珍贵的瓷器,生怕弄疼了昏迷中的人。他那张洗干净了泥污的小脸上,此刻只剩下极致的专注和深不见底的惶恐。每一次听到陈铮那压抑的闷咳,他的身体都会不受控制地瞬间绷紧,擦拭的动作也随之一滞,大眼睛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仿佛那咳嗽声随时会带走眼前之人最后一丝气息。
屋内弥漫着沉重的压抑,只有灶火的噼啪声、药汁的翻滚声、陈铮艰难的呼吸和偶尔的闷咳,以及李狗儿压抑着的、细微的啜泣。
“吱呀——”
一声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打破了屋内的死寂。那扇用破木板拼凑、勉强挡风的木门被推开,一股更加强劲、带着大海深处凉意的风猛地灌入,吹得灶膛的火苗一阵摇曳,也卷起了地上的草屑。
一个高大的身影堵在了门口,挡住了门外灰蒙蒙的天光。
来人是个中年汉子(梁海),身材异常魁梧,骨架宽大,即使隔着粗陋的麻布衣衫,也能感受到那曾经过千锤百炼的肌肉轮廓。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臂——袖管空空荡荡,在灌入的海风中无力地垂落、飘荡。他脸上布满了被海风盐粒和岁月刻下的深纹,一道狰狞的刀疤从左边眉骨斜斜划下,险险避过眼睛,一首延伸到耳根,如同一条丑陋的蜈蚣,为他平添了十分的凶悍与沧桑。他的眼神,却如同海岸边历经千万年冲刷的礁石,沉静、冷硬,深不见底,仿佛蕴含着无尽的风暴与死寂。
他迈步走进屋内,沉重的脚步踩在泥地上,发出闷响。目光如同实质般,瞬间越过灶边的老梁和跪在炕边的李狗儿,牢牢钉在了土炕上昏迷不醒的陈铮身上。那目光锐利如刀,带着一种经历过血火淬炼的、近乎冷酷的审视。
当他那沉静的目光最终落在陈铮肋下——那被厚厚包裹、却依旧被不断渗出的暗红与黄浊液体浸透、散发着淡淡腥腐气味的布条上时,梁海空荡的左袖管,几不可察地、极其细微地抖动了一下。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同类伤势的本能反应。
他没有说话,径首走到土炕边。高大的身躯带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李狗儿下意识地往旁边缩了缩,小脸上满是敬畏和紧张。
梁海伸出仅存的右手。那只手异常宽厚,布满厚厚的老茧和纵横交错的伤疤,如同覆盖了一层粗糙的铠甲。手指关节粗大,却异常沉稳。他没有丝毫犹豫,极其沉稳地搭在了陈铮在薄被外、那只滚烫的手腕上。
屋内瞬间安静下来。
老梁停下了拨弄柴火的动作,浑浊的眼睛紧张地盯着儿子的动作。
李狗儿更是屏住了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只布满伤疤的大手。
时间仿佛凝固。只有陈铮艰难的呼吸和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
梁海的眉头几不可察地微微蹙起。他手指下的脉搏,浮乱而急促,如同沸水中的滚珠,又时而沉涩迟滞,如同陷入泥沼。指腹下的皮肤滚烫得吓人,却又透着一种内里的虚寒。
良久。
梁海缓缓收回了手。他那张被刀疤破坏、如同礁石般冷硬的脸上,依旧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有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光芒——有对伤势凶险的了然,有对伤者意志力的惊异,或许…还有一丝同为沙场弃卒的悲凉。
低沉的声音,如同从礁石深处发出,在弥漫着药味和海腥气的屋内响起,带着一种经历过生死、不容置疑的笃定:
“骨头…接歪了。”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扫过那不断渗血的肋下,“邪毒入里,盘踞不去,高烧灼烧五脏。再拖下去…”
他的声音没有丝毫起伏,却像冰冷的铁块,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神仙难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