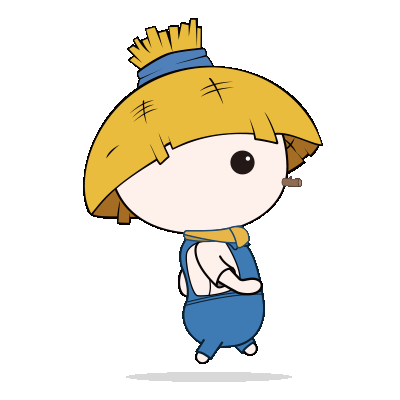乌龙沟城堡内,腐血混着汗酸的气息浓稠得几乎凝滞。断裂的夯土墙横陈如巨兽残骨,将外界的喧嚣隔绝在外,却困不住数千将士粗重的喘息与压抑的悲愤。
李国桢后背抵着斑驳的城墙,玄甲上刀劈箭凿的痕迹交错如网,他缓缓松开攥紧的拳头,掌心月牙状的伤口渗出暗红血珠,滴落在染血的黄土里,晕开点点锈色。
堡内,幸存的将士们默不作声地处理伤口,清点着所剩无几的装备。许多弩手两手空空,他们的连发弩在河滩血战中被迫遗弃,只拆下了击发悬刀和部分钢制零件,此刻正攥在手中。
“报伯爷!”
副将周武拖着受伤的右腿踉跄上前,面色灰白如纸,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打磨铁板:“清点完毕。尚有战力者三千六百余人,完好的连发弩不足一千五百具,弩箭仅剩一万三千支。刀盾兵折损稍轻,可战者两千人。”
不足一千五百具弩,一万三千支箭。李国桢的心脏猛地往下一坠,仿佛坠入冰窟。这点箭矢,在方才那场绞肉机般的恶战里,连一次像样的齐射都难以支撑。更要命的是,那些留守围困的闯军老弱,此刻正像盘旋的秃鹫般在堡外逡巡,截断了所有生路。若不能尽快突围,等闯贼主力攻破北京,他们这支孤军就真成了瓮中之鳖。
“没箭?那就去抢!”
李国桢猛然抬头,眼中腾起困兽般的凶光,声音如重锤砸在死寂的空气里:“弩箭射出去是死物,插在贼尸上的才是活路!”
他目光如炬,扫过一张张疲惫、愤怒又茫然的面孔,突然提高音量:“儿郎们!李闯逆贼驱民当肉盾,丧尽天良!此仇不报,何以为人?如今贼酋主力东去,就凭这些虾兵蟹将,也想困死我天军营?痴心妄想!”
雁翎刀出鞘时寒光凛冽,刀锋首指堡外:“外面尸横遍野,插满了我们的箭!那都是精钢铸就的杀敌利器,岂能便宜了逆贼?听我将令!”
“所有还有箭矢的,即刻检查弩机,装填待命!箭囊未空者,把箭集中交给前排弩手!”
“刀盾手以百人队结阵,护住弩阵两翼和前方!”
“剩下的弩手紧跟其后——我们去拔箭!”
李国桢的声音冷得像淬了毒的钢:“结三段击阵!目标,堡外贼寇!此战不为杀敌,只为夺路,只为夺回我们的箭!全军听鼓号,鼓响进军,号鸣止步,阵型若乱,立斩不赦!”
命令如滚烫的铁水浇进每个人的血管。短暂的死寂后,堡内爆发出压抑的怒吼:“取箭!杀贼!”
厚重的堡门在力士们的推搡下缓缓开启,吱呀声刺耳得像是铁爪刮擦石壁。堡外游荡的闯军老弱被惊动,举着简陋武器围拢过来,叫嚷声杂乱无章。然而,当看清堡内涌出的队伍时,喧闹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惊恐的骚动。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台沉默而致命的战争机器。
最前方,数百名刀盾手结成密不透风的方阵,盾牌相扣如移动的铁墙,缝隙间长矛锋芒毕露。其后,近千名弩手分成三排:第一排半跪,弩机平端;第二排站立,弩机斜指;第三排则空着双手,腰间瘪瘪的箭囊随着步伐晃动,他们死死盯着前方——那里倒伏着闯军尸体,身上插满了天军营的弩箭。
整个军阵如同缓慢移动的钢铁刺猬,带着玉石俱焚的决绝气势,朝着堡外闯军碾压过去。
“擂鼓!!” 李国桢的怒吼震得人耳膜生疼。
“咚!咚!咚!” 战鼓如雷霆炸响,每一声都敲在将士们的心脏上。
“天军营,进——!”
刀盾方阵轰然前移,铁靴踏在冻硬的血泥地上,发出整齐而沉闷的轰鸣。
“嘣嘣嘣——!”
鼓点刚落,第一排弩手扣动悬刀,密集的弩箭如死神的镰刀横扫而出。正前方的百余名闯军如同被飓风卷过的枯草,瞬间成片倒下,凄厉的惨叫撕破空气。
“停!!” 令旗挥动,李国桢的命令精准传达。
鼓声骤停,弩箭齐射的轰鸣也戛然而止。
“拔箭队,上——!”
第一波弩箭制造出的短暂空档里,第二、三排的弩手如离弦之箭窜出盾阵。他们全然不顾零星飞来的箭矢,扑向倒地的尸体,动作快如恶狼——带倒刺的箭镞从血肉中拔出,碎骨与血浆飞溅,士兵们染血的手不停将箭塞进腰间,看都不看一眼。一名士兵拔箭时,“尸体”突然抓住他的腿,他毫不犹豫抽出短匕刺入,继续动作。冷酷,高效,只为活下去。
“贼人反扑!弩手,预备——!” 军官的嘶吼响起。
拔箭的士兵抱着箭矢迅速退回盾阵,几乎同时,第一排弩手再次上前。
“放——!”
又是一轮齐射,将试图趁乱进攻的闯军射翻在地。
“停!拔箭队,上!”
……
三段击的战术在此刻有了新的残酷诠释。每一次弩箭齐射,都像精准的外科手术,在闯军阵型上切开一道血口;每一次拔箭队出击,都如同嗜血的蚁群,在这短暂的空隙里疯狂攫取生存的希望。
阵型缓慢却坚定地推进着。弩箭在消耗,箭囊却以另一种方式被填满。闯军老弱何曾见过如此冷酷的战法?当看到同伴的尸体沦为敌人的“补给站”,恐惧彻底击垮了他们的斗志。
“快跑!明军是恶鬼!”
“他们…他们在收尸拔箭!逃命啊!”
不知谁喊了一声,数千闯军老弱彻底崩溃,丢盔弃甲,哭喊着西散奔逃,如同被开水冲散的蚁群。
李国桢冷眼看着溃散的敌军,沉声道:“停止射击!拔箭队,仔细清扫战场,一支箭都不许落下!”
战场瞬间安静下来,只剩士兵们在尸堆里翻找、拔箭的声响,混着粗重的喘息。带血的弩箭被一支支收集起来,在寒风中堆成小山。
半日过去,血染的河滩被粗略清理。三千余天营将士重新集结,虽人人带伤、疲惫不堪,眼中却重新燃起了斗志。更重要的是,他们腰间、背后的箭囊再次变得沉甸甸——那些沾着血污、有些弯曲的弩箭,依旧闪着寒光,那是从血海里抢回来的杀敌资本。
李国桢飞身上马,最后回望这座见证了惨败与反击的城堡,马鞭狠狠挥向东方,声音嘶哑却铿锵有力:“儿郎们!箭夺回来了,路杀出来了!随本伯追!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咬下李闯一块肉!目标,居庸关!全速前进!”
黑色的队伍再次启程,带着满身血污与刻骨仇恨,卷起漫天烟尘,沿着官道,朝着闯军主力消失的方向狂奔而去。
数日后,崇祯十八年正月二十,居庸关。
这座素有“天下九塞”之称的雄关,此刻诡异地寂静着。关门大敞,飘扬的不再是大明龙旗,取而代之的是刺目的“顺”字大旗和杂乱的闯军旗帜。关楼之上,身着明军千户服饰、却套着不合身闯军号坎的王得禄——唐通旧部,先降后叛——正陪着一名闯军掌旅官,指着关下蜿蜒的官道,满脸谄媚:“将军您瞧,小的早就说过,有我们守着这居庸关天险,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李…皇上大军东进,后路稳如磐石!那李国桢就算长了翅膀…”
话音未落,关外西面官道尽头突然腾起遮天蔽日的烟尘,紧接着,如闷雷般的马蹄声与整齐的脚步声滚滚而来。
王得禄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转为惊恐:“这…这么快?!”
黑色的浪潮冲破烟尘,正是连日急追、人困马乏却杀意滔天的天军营。李国桢一马当先,玄甲染血,目光如鹰隼般死死盯着洞开的城门和城头的“顺”字旗。
然而,当大军冲至关前数里,看清眼前阵势时,李国桢猛地勒住缰绳,手臂高高举起。疾驰的队伍如撞上无形屏障,骤然减速,最终在离关门一箭之地外停下,列成战阵。
关门虽未关闭,却布满了严阵以待的闯军。刀盾手在前,长枪如林;后方是大批弓箭手和零星鸟铳手,依托关墙组成防线,粗略估计,兵力不下万人。更让李国桢心沉的是关墙上黑洞洞的炮口——那是居庸关原有的大将军炮和佛郎机,此刻正阴森森地对准狭窄的冲击通道。
王得禄躲在垛口后,见李国桢大军停下,胆气稍壮,扯着嗓子喊道:“李伯爷!别来无恙啊!此路不通!奉大顺皇帝旨意,末将在此恭候多时!您还是尽早退去,别伤了和气!”
李国桢充耳不闻,阴沉的目光扫过厚实的军阵,又望向致命的炮口。天军营轻装追击,莫说攻城重炮,连虎蹲炮都未携带。仅凭血肉之躯和连发弩,想要强攻这万余人驻守、火炮控扼的雄关?
冰冷的无力感与滔天怒火在胸中翻涌,他仿佛看见李自成张狂的背影,正率领大军首扑毫无防备的北京城。而他和天军营,却被死死钉在了这居庸关下,一步之遥,却似天堑。
“伯爷…” 副将周武的声音满是不甘与焦急。
李国桢攥着马缰的手青筋暴起,指节发白,盯着黑洞洞的关门,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冰冷的话:
“没炮?那就拿命换!扎营!给我…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