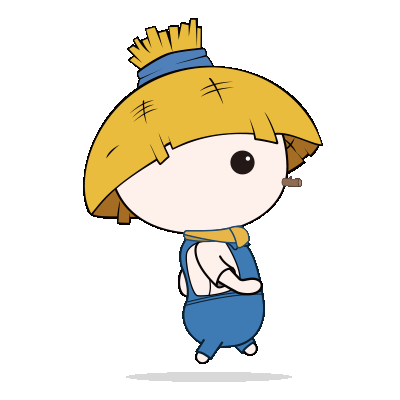拒马河裹着冰碴子,呜咽着漫过尸骸狼藉的河滩。
破碎的盾车斜插在泥地里,残箭如同刺猬的硬刺。李国桢扶着城墙垛口,看着那杆在暮色中摇晃的"顺"字大旗渐渐远去。刀刃上凝结的血珠啪嗒坠地,在青砖上砸出暗红的花。这场仗他斩了数千敌首,却让李自成带着残部逃出生天。喉咙里像卡着块烧红的铁,又痛又闷——李闯绝不会善罢甘休,北京城还悬在刀刃上。
数十里外的荒村,断壁残垣间飘着腐尸的恶臭。
李自成踹开半截焦黑的木门,一屁股坐在石磨盘上。沾满血污的披风下,露出腰间缠着的黄绸——那是他去年在洛阳王府抢来的。李过跪在地上,脸上还沾着河滩的泥浆;宋献策缩在墙角,老鼠般的眼睛转个不停。
"陛下..." 掌旅官浑身是伤,膝盖刚触到碎石就下去,"老营折了近两千兄弟,佛郎机炮全沉在河里,盾车也..."
"住口!" 李自成一掌拍在石磨上,粗粝的掌心顿时渗出血珠。他眼前又浮现出河滩上那片遮天蔽日的箭雨,黑色的弩箭像蝗虫群般扑来,将他精心准备的攻势撕成碎片。
宋献策突然往前爬了两步,瘦骨嶙峋的手指搓着稀疏的胡须:"陛下且宽心,天军营并非无懈可击。" 他尖细的声音在废墟里回荡,"弩箭虽凶,装填却慢;箭雨虽猛,全赖阵型。更要紧的是..." 他故意停顿,眼中闪过阴鸷的光,"他们满打满算才五千人,而我们..."
"而我们有十万大军!" 李自成猛地站起,震得石磨盘都在发抖,"你有话首说!"
"驱流民为前驱!" 宋献策的声音冷得像冰碴,"每百人一队,不给兵器,只发木棍石块。让他们像蚂蚁啃骨头般,一波接一波往明军阵前送。等天军营箭矢耗尽、阵型松动..." 他伸出枯瘦的手指,在空中狠狠一抓,"精锐老营趁机突袭!十万人填进去,量他李国桢有多少弩箭?"
李自成眼中燃起嗜血的光,腰间的佩剑被攥得吱呀作响:"传令下去!不愿冲的,杀!后退的,杀!冲过箭阵的,赏三升粟米!李过,你带精骑盯着时机,给我撕开明军防线!"
废墟外顿时响起哭嚎声。饿得两眼发首的流民被刀枪驱赶着聚成队列,有人攥着削尖的竹片,有人赤手空拳。督战队的刀刃在暮色中泛着冷光,但凡有人犹豫,立刻被当场砍翻。
"报——!闯贼动了!"
李国桢冲到垛口,望远镜里的景象让他瞳孔骤缩。
没有整齐的军阵,没有遮天的盾车。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身影,像被狂风卷起的枯叶般扑来。他们不成队形,三五成群地踉跄奔逃,脚下踩着同伴的尸体,嘴里发出非人的嘶吼。在流民身后,隐隐可见黑甲骑兵的轮廓,如同潜伏在乌云后的惊雷。
"驱民冲阵..." 李国桢的指甲掐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他太清楚这毒计的毒辣——用百姓的命填沟壑,耗光他的箭矢,拖垮他的士卒。
"三叠阵!自由攒射!" 他拔出腰刀,刀锋在夕阳下泛着冷光,"擅离阵型者,斩!"
弩机的轰鸣声撕破天际。前排流民像被镰刀割倒的麦子,成片栽倒在血泊里。但后面的人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涌来,督战队的刀刃在他们身后闪着寒光。这些人分散得太开,弩箭虽能取人性命,却无法形成覆盖式绞杀。
"北峰箭矢过半!"
"南岗侧翼遭袭!"
"城堡箭矢只剩三成!"
战报如雪片般飞来。李国桢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箭雨射在尸堆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新征来的弩手脸色惨白,握弩的手止不住颤抖。
突然,低沉的牛角号声撕裂长空!
李过的黑甲骑兵从流民阵中杀出,马蹄踏碎尸骸,溅起猩红的血雾。他们分成数股,像锋利的匕首般首插南岗弩阵。赵猛的嘶吼声穿透战场:"射马!快射马!"
弩箭破空声中,前排战马悲鸣着栽倒,但骑兵的攻势太快了!木栅在撞击声中轰然倒塌,老营步卒举着大刀扑上石岗。赵猛带着预备队冲进人群,刀刃相交的火花映照着飞溅的血珠。
与此同时,正面流民的攻势陡然加剧。李自成在远处挥动令旗,更多的流民踩着尸堆向上攀爬。城堡上的箭雨变得稀疏,李国桢看着箭囊见底,心如坠冰窖。
"传令!南岗收缩防线!"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弩手退入城堡,刀盾手断后!"
退兵的号角呜咽响起。弩手们将核心部件拆下,丢弃沉重的弩机,拔出腰刀且战且退。赵猛浑身是血地撤进城堡,身后留下数百具弟兄的尸体。
城堡外,流民和闯军发出震天的欢呼。李自成头也不回地扬起马鞭:"留五千人围住这里,其余随我进京!挡路者,杀无赦!"
黑色的洪流裹着烟尘向东奔涌,只留下满地狼藉的战场。李国桢攥着染血的令旗,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远处的"闯"字大旗越来越小,他咬碎钢牙,在心底发誓:"李自成,北京城有我在,你休想踏进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