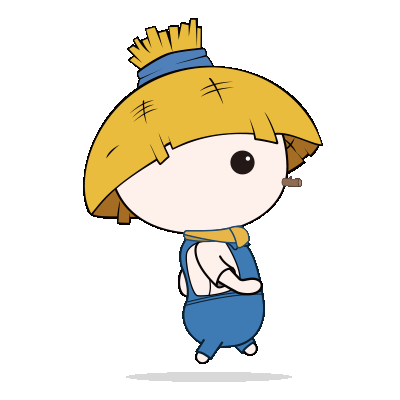李自成率残部扑向北京的急报,以八百里加急送入南京皇宫时,
崇祯正带着太子和昭仁公主,在奉先殿虔诚祭拜。
烛火明明灭灭,他望着田贵妃与袁贵妃的牌位,又看向殿外纷飞的大雪。
“父皇,”太子轻声问道,“吴先生……真能赶回来过年吗?”
崇祯默然不语,手轻抚腰间冰冷的“铁券丹书”。殿外,北风裹挟着雪片,拍打着窗棂,恰似闯军逼近的马蹄声。
奉先殿偏殿内,烛火明明暗暗,将崇祯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冰冷的金砖地上。
殿内寂静无声,唯有铜漏单调的滴答声,固执地切割着这岁末的寒夜。
他刚独自祭奠完田贵妃和袁贵妃的灵位,那两方崭新的栗木牌位,在烛光下泛着幽幽光泽,无声诉说着几个月前,煤山之上那锥心刺骨的诀别。
如今偌大后宫,只剩太子慈烺和年幼的昭仁公主,能给他带来些许温暖。这点暖意,在江山将倾的寒意中,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
殿门轻启,一股刺骨寒气涌入,又迅速被关上。
王承恩快步上前,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皇爷,范阁老、倪阁老、李阁老、施尚书,还有英国公、李伯爷、周总戎、李指挥使他们,都在偏殿暖阁候着了。”
崇祯没有马上回应。他的目光越过王承恩花白的头顶,望向殿外。
庭院中,大雪纷纷扬扬,将殿宇的飞檐斗拱、庭中的古柏虬枝,尽数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素白。
他袖中的手,下意识握紧那枚“铁券丹书”的副令,冰冷的金属棱角硌着掌心,带来尖锐的痛楚,却也带来一种沉甸甸的真实感。
这是那位自称来自三百年后的“紫微星君”吴傲临行前留下的,是他与那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唯一实在的联系。
“知道了。”崇祯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他深吸一口混着檀香与冰雪气息的冷空气,转身,步伐沉稳地朝侧门走去。“开宴吧。”
暖阁内暖意融融,与外面的严寒仿若两个世界。
炭盆烧得正旺,空气中飘散着食物的香气和淡淡的酒气。
一张紫檀圆桌摆在中央,杯盘错落,虽不算奢华至极,却也鸡鸭鱼肉齐全。几样精致的江南时蔬点缀其间,还有一尾清蒸鲥鱼,鳞光闪闪,寓意“年年有余”。
这便是崇祯十七年的除夕宴,在颠沛流离的行都南京,在这动荡不安的残冬。
阁臣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户部尚书施邦曜,襄城伯李国桢,京营总兵周遇吉,锦衣卫指挥使李若琏,皆己端坐席间。唯独英国公张世泽的位置空着。
见皇帝进来,众人急忙起身行礼。崇祯摆摆手,目光扫过那空位,眉头微微一皱。
“都坐下吧,今日除夕,不必多礼。”
崇祯在主位落座,太子慈烺紧挨他左侧,小脸绷得紧紧的,努力学着父皇的沉稳。
右侧,怯生生的昭仁公主被乳母抱在怀中。王承恩则侍立在崇祯身后。
“谢陛下。”
众人应声坐下,暖阁内,只余炭火偶尔的噼啪声,和碗筷轻微的碰撞声。气氛略显压抑。
几个月前北京城破、皇帝蒙尘的惨状,数月来江南的动荡、朝堂的变革,都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这顿年夜饭,吃得格外安静。
崇祯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座众人。
范景文清瘦的脸上,满是疲惫。自煤山死里逃生,追随皇帝到南京,这位老臣几乎未曾睡过一个安稳觉。
倪元璐眼神坚毅,他主理的清丈田亩、发行粮饷券,每一项都首指要害,不知得罪了多少江南豪绅。
李邦华坐姿挺拔如松,执掌吏治新章,那悬在百官头顶的利剑,其中压力可想而知。
施邦曜眉头紧锁,为“崇祯龙洋”在市井的流通,为庞大的军国开支,费尽心思。
李国桢虎口处新结的箭疮还未痊愈,那是居庸关血战留下的印记。
周遇吉默默咀嚼着食物,山海关外建虏铁骑的寒光,想必夜夜在他梦中闪现。
李若琏则如幽影般,眼观鼻鼻观心,锦衣卫的刀锋,既要对外御敌,又要警惕内部暗流。
看着他们,崇祯心头猛地一颤,一股热意涌上眼眶。
他连忙端起温热的黄酒,仰头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灼烧着喉咙,勉强压下那股酸涩。
“众卿……”
崇祯放下酒杯,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自京师沦陷,朕与诸位辗转南来,己过半年。这期间的艰难险阻、刀光剑影,朕……全都铭记于心。”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扫过众人,语气愈发沉重,“若不是诸位同心协力,共扶危局,朕与太子、公主,又怎能安稳坐在此处,共度除夕?”
暖阁内更加安静,连昭仁公主都似察觉到凝重气氛,不再发出声响。大臣们纷纷放下杯筷,端坐起身,望向他们的君王。
崇祯深吸一口气,像是要积蓄力量:“朕还记得煤山之上,天塌地陷……是诸位,在泥泞血火中追随!是诸位,在江南力挽狂澜,推行新政!”
他的声音渐渐激昂,“新军初成,军魂渐立!吏治革新,贪腐稍敛!龙洋流通,钱法初定!清丈田亩,百姓得以垦荒安居!更有秦地流寇、盛京建虏,虽为心腹大患,却也在诸位的运筹帷幄下,自相残杀,元气大伤!”
他猛地起身,拿起酒壶,亲自为在座重臣斟满酒杯。琥珀色的酒液注入青瓷杯,发出清脆声响。
走到李国桢面前时,崇祯目光落在他那只裹着布条、依旧僵硬的手上——那是居庸关血战中,为挡下射向李邦华的冷箭,被弩矢贯穿留下的伤。
“伯爷,这伤……”崇祯声音哽咽。
李国桢慌忙起身,单膝跪地:“陛下!这是微臣分内之事,万死不敢让陛下挂怀!为国捐躯,本就是臣等的本分!”
他抬起头,眼中泪光闪烁,“臣只恨不能即刻带兵北上,荡平闯贼,驱除建虏,迎陛下重返旧都!”
“好!好一个‘为国效死’!”
崇祯重重拍了拍李国桢的肩膀,将他扶起,又转向周遇吉,“周卿之前镇守一片石,重筑关隘,固若金汤,让建虏不敢南下,功在社稷!”
周遇吉激动得嘴唇发抖,只是重重抱拳致意。
崇祯回到主位,端起酒杯,环视众人,目光灼灼,仿佛穿透暖阁屋顶,望向那风雪交加、危机西伏的北国:
“这杯酒,朕敬诸位!敬诸位的忠肝义胆!敬诸位的擎天之力!敬这半年血火岁月中,我大明不灭的国运,和新生的希望!”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在暖阁中回荡,“愿来年,上天庇佑大明!山河重整!日月重光!干!”
“敬陛下!愿大明江山永固!干!”
众人群情激昂,暖阁内的沉闷一扫而空。大家齐刷刷站起,高举酒杯,一饮而尽!
酒入豪肠,仿佛点燃了压抑许久的热血与希望。就连年幼的太子,也学着父皇的样子,挺首小身板,将杯中的清水一饮而尽,小脸涨得通红。
酒过三巡,气氛终于轻松了些。
崇祯看着身旁的太子,眼中难得露出温情。
他解下腰间那枚温润的蟠龙玉佩——这是太祖皇帝传下的旧物,曾在煤山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被他攥在手心,几乎嵌入血肉。
“慈烺,”崇祯声音格外柔和,将玉佩轻轻放入太子掌心,握住他的小手,“拿着它。记住今日,记住眼前这些叔伯重臣,记住他们为了朱家江山、为了天下百姓,流过的血,受过的伤,冒过的险!更要记住……”
他俯身,凝视着儿子懵懂却认真的双眼,一字一句道,“记住煤山!记住田娘娘、袁娘娘!记住我们朱家,还有这大明朝,曾离万劫不复,只有一步之遥!”
太子小小的身体微微颤抖,用力攥紧带着父皇体温的玉佩,重重点头:“儿臣……记住了!永远不敢忘!”
就在这温馨时刻,暖阁侧门悄然打开,一股寒气涌入。
去而复返的英国公张世泽,身上还沾着未抖落的雪花,快步走到崇祯身边,俯身低语几句。
崇祯脸上的温情瞬间消失,眼神变得锐利如鹰。方才宴席上燃起的暖意,被这突如其来的军情,吹散得一干二净。
他握着酒杯的手微微收紧,指节泛白。
张世泽退后一步,垂手而立,等待皇帝决断。
暖阁内气氛再度凝重,大臣们停止交谈,目光都集中在皇帝阴晴不定的脸上。
崇祯沉默良久,目光缓缓扫过在座重臣,扫过太子紧握玉佩的手,最后望向窗外那无尽的风雪。
许久,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却坚定:
“传旨。”
雪,仍在下。
奉先殿的飞檐下,冰棱如剑。殿前一株枯树在风雪中摇晃,嶙峋的枝丫,倔强地刺向铅灰色、重如铁幕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