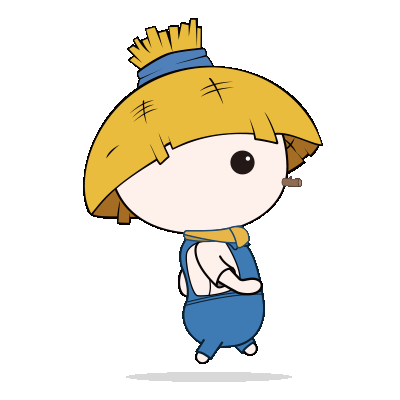沈珩说苏月妩想不出还错在何处就不放她出养心殿,还真就言出必行。
入夜,张贵德满面堆笑拦着殿门:“娘娘回去吧,这天都黑了,还刮着风,说不定一会儿就要下雨了,还是养心殿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您就别走了。”
苏月妩朝外面看了眼,果然闷风阵阵, 树叶扑簌簌作响,天上也没有月亮,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她本也不是真要走,就故作遗憾地叹了口气,回内殿去了。
沈珩在批折子。
听见动静掀起眼皮看了她一眼,阴阳怪气道:“走啊,怎么不走了?”
苏月妩坐到他旁边,抱住他的胳膊用头蹭了蹭,语气迷茫地问:“谁要走了?嫔妾哪儿要走了?嫔妾只是想散散步,好好想想自已错在哪儿了而已。”
沈珩冷哼,但唇角却不由自主勾了勾。
苏月妩发现自已现在还是很喜欢装模作样逗沈珩玩儿,可是这装模作样又和以前不同。
区别就在于,如今自已也乐在其中了。
外面的风有些大了,张贵德关上外殿的门走进来,见两人这相处的模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陛下,不知这次婕妤娘娘要留宿养心殿几日,可要去钟粹宫唤个宫女来侍奉?”
沈珩不说话,瞥了苏月妩一眼。
那意思很明显,你说留几日?
苏月妩讨好地笑了笑:“陛下,嫔妾明日还得回钟粹宫一趟,家里的冯姨娘不日要回青州我舅舅家去,我想把进宫来得的一些赏赐整理整理,让她顺便捎带去,毕竟当初我入宫的时候,是舅舅赠了我千两白银,也算聊表感激之意。”
沈珩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你想明白自已错哪儿了吗,说走就走?”
苏月妩顿了顿,轻咳一声,抬头对张贵德道:“张公公,您先下去吧,顺手把槅门关上。”
张贵德赶紧朝沈珩投去询问的目光。
沈珩瞪了他一眼。
张贵德瞬间会意,低头哈腰“嗻!”了声,就赶紧退了下去,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这回有了经验,他把小太监撵得远了点,免得一会儿陛下叫起来,他也跟着尴尬。
殿内。
沈珩心不在焉地用朱笔写下“朕知道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就把手中折子扔到一边,微红着耳尖道:“朕还没有消气呢,不许动手动脚。”
苏月妩思索片刻,勉为其难妥协了:“也不是不行。”
……
“不行!!!”
沈珩猛地站起身,浑身僵硬发抖,颤颤地用手去系衣带,因为太过惊惧,脸上的红都没了,变得刷白一片。
他胡乱系好衣带,看向蹲在自已腿前的苏月妩,待视线扫到那两瓣红唇,心就像是被狠狠扎了一下似的,眼眶都红了。
苏月妩没想到他反应那么大。
关键是并不像兴奋的。
她皱了皱眉,有些疑惑,书里明明写男子很喜欢这样的,就是父亲从青楼请来的那个女教习,所传授的第一课也是这个。
沈珩快步去桌前倒了杯茶水回来,蹲下身递到她唇边,哑声道:“漱一漱,脏。”
苏月妩笑眼看他:“怎么脏了,我也就……”
沈珩已经把茶水怼到了她唇边。
苏月妩只得依言漱口。
沈珩挪了痰盂过来接着,等她漱完口,又倒了一杯茶,让她接着漱。
漱到苏月妩烦躁时,他才又去找了条巾子在珐琅彩盆里浸湿,回来给她擦拭唇瓣。
苏月妩想说话,但被他一直摆弄着嘴也没法开口,只能睁眼看着他。
沈珩面色难看极了,眼圈发红,紧紧盯着自已的唇,像是擦不干净就要哭了。
至于吗……
好不容易等他撒开手,又去换了条巾子浸水,苏月妩终于能开口了,笑问:“再擦就破皮了,你就这么嫌弃你自已?”
沈珩拧巾子的动作顿了顿,良久,嗓音低哑地道:“阿妩,朕之前……幸过别的嫔妃……”
做太子时的他,根本违抗不了君父之命,让他娶谁为妻,让他纳谁为侍妾,他都要照做。
若稍有违逆,遭难的便是他身边的亲近之人。
沈珩见过父皇后宫的很多妃嫔。
她们有的甚至一辈子就见过父皇一面,被帝王一时兴起点入宫中,便抛之脑后。
凄凄清清一辈子,有的疯傻了,有的疯魔了。
沈珩厌恶父皇到极致,不愿和他一样。
既然迫于无奈娶了,他便要负起责。
所以即便没有感情,他也幸过她们。
如果能怀上皇嗣,终身有靠是她们的命,如果不能,他锦衣玉食的供养着,也不算亏待了。
他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阿妩还能回到自已身边,跟他破镜重圆。
早知如此……
沈珩闭了闭眼,心中涌起无限的痛悔。
苏月妩愣了愣。
她深呼吸,稳了稳心绪:“我早就知道呀,不然皇子和公主是哪来的。”
她的语调太过轻松,甚至还带着宽解他的意思,沈珩心口一阵闷窒,对着水面中映照出的自已的轮廓,轻声问:“你一点都不介意?”
苏月妩目光微微迟疑了一下,知道他想听什么答案,但或许是因为上午两人的谈心,此刻,她不是很想装模作样的拈酸吃醋。
她只平静地问道:“如果我介意的话,难道你会遣散后宫?”
沈珩一顿。
苏月妩无奈地叹了口气:“沈珩,我知道你想让我认什么错,你无非是觉得我没有像三年前那样想强势的独占你,便是没有十分真心,可你得知道,我要还和那时候一样,可就不止会吃醋了,我还会嫉妒,看到你和其它妃子在一起就发疯,说不定还会仗着你的宠爱欺负她们,在后宫横行霸道,你愿意我这样吗?”
沈珩心头微动。
他垂落眼睫,不可避免地按照阿妩所说的话去幻想,她仗着自已的宠爱作天作地,吃醋发疯,想着想着,唇角就忍不住轻轻上扬了。
而在苏月妩的眼里,沈珩背对着自已,被堵住了哑口无言。
她只得又放缓声音,言语半真半假地劝道:“沈珩,我现在对你已经在用真心了,只是我得时刻克制警醒自已,你是帝王,是天下的君父,所以我要豁达明事理,你就安生点儿,别招惹我变成那样了,行吗?”
话音刚落,沈珩就把帕子扔到了水盆里,转过身眸色幽暗地盯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