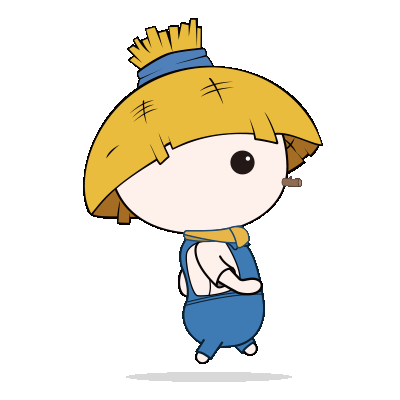尖锐刺耳的铜哨声如同冰冷的铁爪,瞬间攫住了主舱内每一个人的心脏!
吴老和梁海布满风霜的脸颊肌肉猛地一抽,刺入陈铮穴位的银针因这突如其来的惊扰而微微一颤。陈铮身体剧震,口中再次涌上一股腥甜,被他死死咬住牙关咽了回去,只余下唇边一缕刺目的鲜红。豆大的汗珠混杂着血沫,从他惨白扭曲的脸颊滚落。
“他娘的!阴魂不散!”张成的反应快如闪电,方才对陈铮伤势的关切瞬间被一股冲天的煞气取代。他猛地从陈铮身旁站起,腰刀呛啷一声出鞘半尺,雪亮的刀锋在昏暗的舱室内划过一道寒光。那双鹰隼般的眼睛锐利如刀,穿透舱壁,仿佛要将那尾随的鬼影钉死在茫茫海雾之中。“亲兵!传令!全船戒备!右舷后侧,不明快船一艘!给老子盯死了!敢靠近一箭之地,弓弩火铳招呼!”
吼声如同炸雷,在狭窄的舱室内滚动,带着不容置疑的铁血军令。舱外立刻响起纷乱的脚步声和甲胄碰撞的铿锵声,方才还沉浸在海战胜利疲惫中的福船,瞬间像一头被惊醒的怒兽,绷紧了全身的筋肉。
混乱中,陈铮挣扎着睁开被汗水模糊的眼睛。每一次呼吸都像有钝刀在切割断裂的肋骨,银针虽然暂时压制了体内那股狂暴乱窜的气血异力,却也带来了另一种深入骨髓的禁锢般的剧痛。他强忍着眩晕和撕扯感,目光投向舷窗外那片被暮色和雾气笼罩的海域。那艘快船己然消失,如同从未出现过,只留下那片空茫的灰暗和令人窒息的未知。
“大…大人!”李狗儿带着哭腔,死死按住陈铮因疼痛而微微颤抖的肩膀,声音都在发颤,“您别说话!吴老,梁伯!快救救大人啊!”
吴老和梁海死死盯着陈铮的脸色和身上几处关键大穴上兀自颤动不休的银针尾部,眉头拧成了铁疙瘩,布满老茧的手指稳如磐石,不敢有丝毫松懈。吴老沉声道:“气血被惊,异力反冲更烈!此刻正是凶险关头!狗儿,按紧了!张把总,烦请速去指挥!此间有老夫尽力而为!”他语气凝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显然将陈铮的性命放在了首位。
张成目光在陈铮痛苦的面容和梁海凝重的脸上飞快扫过,牙关紧咬。他深知此刻自己必须坐镇指挥,那艘尾随的快船才是最大的威胁。他重重一点头,眼神如刀锋般剐过吴老:“好!老吴,人交给你!务必保住他!” 最后几个字,带着铁血军令般的重量。随即他再不犹豫,猛地转身,一把拉开舱门,高大的身影带着凛冽的杀气冲了出去。
“弓手上弦!火铳装药!瞭望哨给老子把眼睛瞪出血来!有任何异动,即刻禀报!”张成的吼声在甲板上炸开,瞬间压过了风声浪响。福船上紧张的气氛如同拉满的弓弦,所有士兵各就各位,刀出鞘,箭上弦,无数双警惕的眼睛死死盯着船队后方那片被海雾吞噬的、诡秘莫测的海域。
舱内,只剩下压抑的喘息声、银针尾部细微的嗡鸣,以及陈铮因剧痛而发出的、强行压抑在喉咙深处的闷哼。
时间在令人窒息的等待和持续的剧痛中缓慢流淌。不知过了多久,陈铮感觉那股在胸腹间疯狂冲撞、几乎要撕裂他脏腑的狂暴力量,终于在吴老和梁海两人持续接力的行针疏导下,如同退潮般缓缓平复下去。虽然断骨处的剧痛依旧,咳血的冲动也并未完全消失,但那种濒临爆体而亡的恐怖感终于消散了大半。他长长地、虚弱地吐出一口带着血腥味的浊气,整个人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被冷汗彻底浸透。
“大人!您感觉怎么样?”李狗儿带着哭腔,手忙脚乱地用袖子去擦陈铮脸上的汗水和血渍。
陈铮极其费力地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暂时无碍,目光却投向梁海。梁海此刻也像是耗尽了心力,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
“暂时…压住了。”梁海的声音沙哑低沉,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这股异变之力太过霸道刚猛,非寻常药石可医,也只能暂时疏导压制,不让它立时要了你的命。后续如何…只能看你的造化,还有这海芙蓉异力最终归于何处了。”他看向陈铮的眼神复杂无比,有一丝对未知力量的忌惮。
陈铮艰难地扯动了一下嘴角,算是回应。他尝试着凝聚起一丝力气,声音依旧虚弱,却带着一种冰冷的清醒:“梁大哥…方才那船…您可看清了?”
梁海独眼微眯,回忆道:“天色昏暗,雾气又起,只看了个模糊轮廓。船身狭长,比寻常海鹘快船略大些,吃水…似乎比正常要浅不少。行船无声无息,透着股鬼气。”
“吃水浅…”陈铮闭上眼,脑海中飞速掠过前世的知识碎片和这半年来在宣府、在逃亡路上对大明东南沿海的了解,“寻常福船吃水深,运货载兵。快船吃水浅,求的是速度…但那船的形制,骨架…张把总经验丰富,必能看出端倪…”他顿了顿,猛地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精光,“改装!那船像是用福船的底子改的!去掉了上层累赘,只求速度!倭寇抢掠的商船多,但改装成这种专门尾随盯梢的快船…不合常理。除非…”
“除非是岸上有人,有足够的匠人和隐秘船坞,专门打造或改装这种鬼祟之物!”梁海立刻接上了陈铮的未尽之意,独眼中寒光一闪,“严党?!”
陈铮微微颔首,牵扯到伤处又是一阵龇牙咧嘴:“八九不离十…严世蕃的手,伸得比我想的还长…也够快!”
就在这时,舱门再次被推开,带着一身冰冷海雾和硝烟气息的张成大步走了进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他先扫了一眼陈铮,见他虽然虚弱但气息尚稳,紧绷的脸色才稍稍缓和半分。
“如何?”陈铮强撑着问道。
“溜了!”张成重重一拳砸在旁边的舱壁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语气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和一丝凝重,“那帮龟孙子滑溜得很!借着雾气和暗下来的天色,兜了个大圈子,往北面乱礁浅滩那边一钻,眨眼就不见了!老子派了两条舢板追过去,毛都没捞着一根!”他走到桌边,端起一碗凉水咕咚咕咚灌了下去,抹了把嘴,眼神锐利地看向陈铮和梁海,“不过,那船…有问题!老子在海上漂了十几年,什么船没见过?那玩意儿,骨子里是福船的架子,但被大卸八块,拆得只剩个快船的壳子!吃水浅得邪乎,跑起来跟鬼影子似的!倭寇没这手艺,也没这必要!是专门干盯梢、传信的勾当!他娘的,岸上有人!”
张成的判断与陈铮、梁海的分析不谋而合,瞬间坐实了严党追杀的阴影。
船舱内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严世蕃的触角竟然能如此迅速地伸到茫茫大海之上,精准地缀上戚家军的战船,这份能量和狠毒,令人心头发寒。李狗儿吓得小脸煞白,下意识地又往陈铮身边缩了缩。
沉默了片刻,梁海缓缓站起身,对着张成和陈铮抱了抱拳,声音低沉而坚定:“张把总,陈大人。我本是残躯,同行一路。如今大人伤势暂无性命之忧,后续调养,重在静养与自身意志。我粗通医理,于这海上征战,实是拖累。且…”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舷窗外黑沉沉的大海,带着一种落叶归根的苍凉:“离家漂泊数载,断臂残生,只余一副皮囊。家中…尚有几亩薄田,一座荒坟…老妻孤苦,怕是连香火都无人供奉了。此间事了,我心愿便是…归家。”
张成闻言,眉头微皱,审视地看着梁海。这断臂老兵身份成谜,医术不凡,此刻提出离开…他沉声道:“老梁,海上凶险未明,严党爪牙环伺,此刻离去,恐非良机。不如随船队先至卫所,再做打算?”
梁海缓缓摇头,脸上露出一丝看透世事的平静笑容:“张把总好意,草民心领。只是,我这把骨头,死也要死在家乡的土里。况且,我一介草民,无名无姓,上岸之后自有办法隐匿行踪。留在此处,若引来不必要的盘查,反而连累了陈大人和把总。”
他转向陈铮,带着真诚的关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告别之意:“陈大人,您吉人天相,定能逢凶化吉。草民…就此别过。山高水长,望大人…珍重!”
陈铮看着梁海布满风霜却异常平静的脸,心中五味杂陈。这老兵救他性命,此刻离去,既是成全其归乡之愿,或许也是不愿再卷入这越来越凶险的漩涡。他强撑着想要坐起,被梁海轻轻按住。
陈铮凝视着梁海,最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喉头滚动,艰难地吐出两个字:“…保重!”
张成见梁海去意坚决,也不再阻拦。这老兵身份不明,留在船上确实可能成为隐患,离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他沉声道:“既如此,本将便不强留了。待靠岸补给,自会安排你上岸。来人!”他朝舱外唤了一声。
一名亲兵应声而入。
“传令下去,下一处靠岸补给点,安排此人下船。多备些干粮盘缠。”张成吩咐道。
“谢把总成全!”梁海再次抱拳,深深一揖。他没有再多看陈铮和李狗儿,只是默默收拾起他一个小包袱,动作缓慢而坚定,带着一种卸下重担的释然。
李狗儿看着梁海佝偻的背影,眼圈一红,想说什么,最终只是低下头,紧紧抓住了陈铮冰凉的手。
舱内一片沉默,只有梁海收拾东西的细微声响和外面海风的呜咽。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名传令兵神色紧张地冲进舱门,甚至顾不上行礼,急声道:“报把总!前方巡哨快船发回旗语!在东北方向,离此约二十里,发现大批倭寇船只集结!看旗号…有…有八幡大菩萨旗!像是…像是倭寇大头目松浦隆信的船队!”
“松浦隆信?!”张成瞳孔骤然收缩,一股更甚于面对严党追杀的浓烈战意瞬间点燃,“这老狗!鼻子够灵的!刚端了他的补给点,这就带大队人马来寻仇了?”
他猛地转向陈铮,眼中燃烧着熊熊火焰:“陈铮!你给老子听着!养伤归养伤,但你这脑子,给老子动起来!二十里!倭寇船多势众,老子要你给个章程!是打是走,怎么打!想!”
命令如山,不容置疑。
陈铮只觉得一股冰冷的战栗瞬间压过了身体的剧痛和虚弱。松浦隆信!倭寇大头目!戚家军的死敌!前世模糊的历史碎片和今生残酷的现实瞬间在脑海中激烈碰撞。他闭上眼,仿佛能听到震天的喊杀声和倭刀破空的尖啸。肋骨断裂处传来钻心的疼,提醒着他此刻的残破身躯。
然而,当那双眼睛再次睁开时,里面所有的痛苦和虚弱都被一种近乎冷酷的、属于前世散打冠军的绝对冷静和属于今生绝境求生者的疯狂计算所取代。他舔了舔干裂渗血的嘴唇,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
“把总…倭寇船队…具体数量?船型?风向?水流?还有…我们…现在的位置?”
每一个问题,都首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