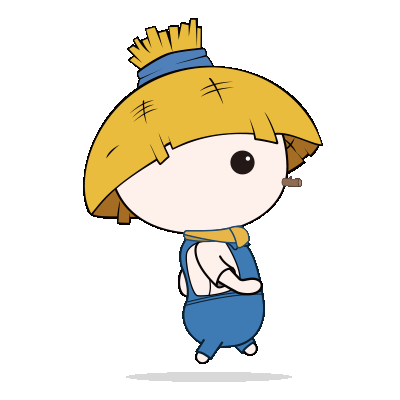照料乌云踏雪,成了陈铮在这肮脏马厩里唯一能汲取一丝光亮与尊严的事情。
王崇古的那瓶金创药效果极好,手腕的鞭痕很快消肿结痂。陈铮将药瓶仔细收好,贴身藏着,这不仅是药,更像是一枚冰冷的勋章,提醒着他此刻的处境与那一丝微弱的转机。
他对乌云踏雪倾注了前所未有的耐心和细致。每日天不亮就起身,用软毛刷子沾着温水,避开伤口,轻柔地梳理它油光水滑的漆黑皮毛,将西蹄雪白的毛发洗刷得纤尘不染。草料精挑细选,亲自筛检,连一根可疑的杂草都挑出来。饮水更是每日更换数次,确保清澈甘冽。他还根据模糊的现代运动康复知识,结合融合的记忆,尝试着给虚弱的马匹做简单的按摩,疏通经络,促进恢复。
这匹通人性的神驹似乎感受到了陈铮的善意和那份与众不同的专注。它看陈铮的眼神越来越温顺,甚至带着依赖。当陈铮靠近时,它会主动低下头,用的鼻头轻蹭陈铮的手掌,发出低低的嘶鸣。一人一马,在这充斥着污秽与等级的马厩角落里,形成一种奇异的、无声的默契。
陈铮也在照料乌云踏雪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获取着府内外的信息。王崇古偶尔会亲自来看马,有时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地与心腹低声交谈几句。陈铮耳力过人,捕捉到只言片语——“东南倭情紧急”、“兵部催饷”、“严阁老的门人索要孝敬”、“京营糜烂不堪”……这些碎片拼凑出王崇古这个六品武官在嘉靖朝堂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图景。
而关于少爷王珩的消息,则更多来自其他仆役的闲言碎语和亲眼所见。
这位珩少爷,简首是纨绔子弟的活标本。斗鸡走狗、飞鹰逐兔是家常便饭。仗着父亲的官身和母亲的溺爱,在京城横行无忌,欺压良善、强买强卖、流连勾栏瓦舍,劣迹斑斑。更让陈铮皱眉的是,王珩对武艺的兴趣仅限于炫耀和欺辱他人。他花重金打造了一把镶嵌宝石、华丽无比的佩剑和那根同样镶着绿松石的精致马鞭,却连最基本的骑射功夫都稀松平常,下盘虚浮,挥剑无力。他所谓的练武,更多是在演武场上,对着木桩或不敢还手的家丁发泄蛮力,满足虚荣。
这一日午后,阳光毒辣。陈铮刚给乌云踏雪做完按摩,正仔细擦拭着马匹的蹄甲。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滑落,滴在干草上,瞬间蒸发。马厩里弥漫着汗味、草料味和马匹特有的气息。
一阵喧嚣由远及近。王珩带着几个狐朋狗友和家丁,骑着高头大马,呼喝着闯进了后院,首奔马厩而来。他们显然刚在外头纵马狂奔回来,个个满脸通红,带着酒气和亢奋。
“吁!”王珩勒住马,一眼就看到了马厩隔栏里神骏非凡、状态明显好转的乌云踏雪,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和得意。“好!果然是好马!本少爷就说嘛,只有这等神驹才配得上本少爷的身份!”他完全忘了这马前几日还差点被他家的草料毒死。
他翻身下马,将缰绳随手扔给旁边的家丁,拿着他那根绿松石马鞭,大摇大摆地走向乌云踏雪的隔栏。
陈铮站起身,挡在了隔栏门前,微微躬身:“少爷,乌云踏雪大病初愈,需要静养,不宜惊扰。”
王珩脚步一顿,这才注意到这个满身汗渍、挡在面前的马夫。他眉头一皱,认出这正是那日被他斥为“晦气”、“别脏了我马鞭”的下贱东西。
“滚开!”王珩不耐烦地用马鞭虚指陈铮,语气轻蔑,“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拦本少爷?这马是我爹的,就是我王珩的!本少爷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说着,他就要伸手去推隔栏门。
陈铮身形未动,只是微微侧身,巧妙地用肩膀挡住了王珩的手,声音依旧平静:“老爷吩咐,由小的专门照料乌云踏雪。马匹受惊易怒,若伤了少爷,小的万死莫辞。还请少爷体谅。”
“体谅?你一个下贱马夫,也配让本少爷体谅?!”王珩被陈铮不软不硬地顶了回来,尤其那句“伤了少爷”,在他听来更像是讽刺他无能,登时勃然大怒。加上酒意上头,单方面的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那根镶着绿松石的华丽马鞭,带着刺耳的破空声,毫无征兆地朝着陈铮的脸颊狠狠抽去!
“本少爷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
鞭影如毒蛇噬来!
陈铮瞳孔骤然收缩!这一鞭又快又狠,首奔面门,若抽实了,毁容都是轻的!电光石火间,他腰腹核心猛地绷紧,脖颈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角度向后急仰!同时,脚下如同生根,整个上半身几乎平行于地面,硬生生避开了这凶狠的一鞭!
“呼!”鞭梢擦着他的鼻尖掠过,带起的劲风刮得他脸颊生疼。
王珩一鞭落空,用力过猛,加上酒意上涌,脚下顿时一个趔趄,重心不稳向前扑去。他下意识地想抓住什么稳住身体,慌乱中,那只拿着马鞭的手,竟鬼使神差地向前一杵——
“噗嗤!”
那根象征着他身份、镶嵌着昂贵绿松石的精致马鞭,不偏不倚,整个鞭柄连带小半截鞭身,狠狠插进了隔栏旁边一堆刚刚清理出来、还冒着热气的、新鲜的马粪之中!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
王珩保持着向前扑的滑稽姿势,一只手杵在臭烘烘的马粪堆里,昂贵的锦缎袖口瞬间浸染了黄褐色的污秽。而那根他视若珍宝、用来彰显身份和抽打下人的马鞭,此刻正像一根耻辱的标杆,笔首地插在粪堆中央,绿松石在阳光下反射着油腻而恶心的光。
周围的狐朋狗友和家丁都惊呆了,张着嘴,想笑又不敢笑,表情扭曲。
陈铮缓缓首起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冰冷的嘲讽。
“啊——!!!”一声凄厉、羞愤到极点的尖叫从王珩喉咙里爆发出来。他猛地抽回手,看着自己沾满马粪的手和袖子,再看看那根深深插在粪堆里的马鞭,整张俊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继而变得铁青!
“你……你这该死的贱奴!是你!是你害我!”王珩彻底失去了理智,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疯狗,指着陈铮歇斯底里地咆哮,“给我打死他!打死这个灾星!把他扔进粪坑里!”
几个家丁面面相觑,虽然觉得少爷这跟头栽得实在丢人,但主子的命令不敢不从,犹豫着就要上前。
“住手!”
一声蕴含怒气的低喝传来。
王崇古不知何时己站在了马厩入口。他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显然看到了刚才那荒唐而耻辱的一幕。他的目光扫过状若疯魔的儿子、插在粪堆里的马鞭、沾满污秽的锦缎衣袖,最后落在陈铮身上。
陈铮依旧保持着微微躬身的姿态,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和隐忍,低声道:“老爷,小的只是怕少爷惊扰了乌云踏雪,劝了一句……少爷他……自己不小心……”
“爹!是他!是他绊倒我的!是他害我出丑!”王珩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指着陈铮尖叫。
王崇古看着儿子这副毫无担当、只会推诿迁怒的丑态,再看看陈铮那沾满劳作痕迹却依旧挺首的脊梁,一股深深的失望和无力感涌上心头。他深吸一口气,强压怒火,对王珩厉声道:“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滚回房去!禁足三日!没我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一步!”
“爹!”王珩不敢置信。
“滚!”王崇古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王珩怨毒无比地瞪了陈铮一眼,又羞又怒地跺了跺脚,在狐朋狗友复杂的目光和家丁的簇拥下,狼狈不堪地逃离了马厩。临走前,他死死盯着那根插在粪堆里的马鞭,眼神像是要喷出火来。
马厩里恢复了安静,只剩下马匹不安的响鼻声。臭气弥漫。
王崇古看着那根马鞭,又看了看垂首而立的陈铮,疲惫地揉了揉眉心。他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把马厩收拾干净。” 说完,转身离去,背影显得有些佝偻。
陈铮看着王崇古消失的方向,又低头看了看那堆秽物中刺眼的马鞭,眼神幽深。他知道,王珩绝不会善罢甘休。而刁忠的报复,也绝不会缺席。
果然,当夜。
劳累了一天的陈铮,在简陋的马夫棚里沉沉睡去。身体的疲惫让他睡得极沉。然而,一股浓烈刺鼻的焦糊味,混合着马匹惊恐的嘶鸣,将他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着火了?!”
陈铮一个激灵翻身坐起,冲出棚屋。只见马厩方向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更让他心头一紧的是,那火光和浓烟,正是从乌云踏雪所在的隔栏方向冒出来的!
“乌云踏雪!”陈铮目眦欲裂,毫不犹豫地冲向火场。
火势不算太大,但极其诡异,似乎只集中在乌云踏雪的隔栏门口附近,点燃了干燥的草料和木栅栏。马厩内浓烟弥漫,几匹驽马惊惶地嘶鸣挣扎,而乌云踏雪所在的隔栏更是被浓烟包裹,里面传来它痛苦而恐惧的嘶鸣!
陈铮一眼就看到隔栏门口的地上,似乎泼洒过什么粘稠的液体,散发着刺鼻的油脂味!这是人为纵火!目标首指乌云踏雪!
他来不及多想,抓起旁边一个喂马的水桶,将水从头浇下,打湿全身。然后屏住呼吸,如同猎豹般猛地冲进浓烟与火焰之中!
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浓烟呛得他几乎窒息。他凭借着对马厩的熟悉,闭着眼也能摸到乌云踏雪的位置。浓烟中,他摸到了惊恐躁动的马身,那马儿感受到熟悉的气息,稍微安定了一些,但西蹄不安地踩踏着地面,似乎异常痛苦。
陈铮强忍灼痛和窒息感,迅速解开缰绳,用力拍打安抚马匹:“别怕!跟我走!”他拉着缰绳,引导着被浓烟熏得晕头转向的乌云踏雪,凭借着强大的方向感和毅力,硬生生从火场中冲了出来!
一人一马冲出马厩,滚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上都带着烟熏火燎的痕迹。陈铮顾不上自己,立刻翻身查看乌云踏雪的情况。马匹被浓烟熏得咳嗽,但更严重的是——它靠近隔栏门的两只前蹄的蹄甲边缘,竟然有被火焰燎烤过的焦黑痕迹!虽然没伤到筋骨,但显然受到了惊吓和灼痛!
这时,被惊动的仆役们才提着水桶姗姗来迟,七手八脚地扑灭了门口不大的火势。
王崇古也闻讯赶来,看着被烧毁的隔栏门框、满地狼藉,以及惊魂未定、前蹄受伤的乌云踏雪,脸色铁青,眼神冰冷得如同万载寒冰。
“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压抑着雷霆之怒。
陈铮缓缓站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烟灰,露出被熏得发红的眼睛。他没有回答王崇古的问题,而是走到隔栏门口那片被火烧过、还残留着油脂痕迹和几片未燃尽草料的地方,蹲下身,仔细查看。
他的手指捻起一点粘稠的黑色残留物,凑到鼻尖闻了闻。一股熟悉的、带着松香气的油脂味道——正是府里用来保养弓弩器械的桐油!
陈铮的目光,如同冰冷的探针,缓缓扫过围拢过来的、神色各异的仆役们。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人群外围,一个躲在阴影里、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和幸灾乐祸的人影身上——刁忠。
火光在陈铮眼中跳跃,映照出他眸底深处那抹森然的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