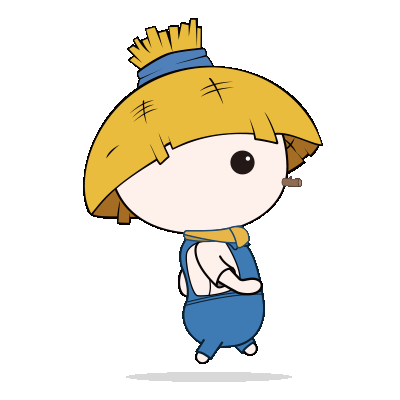回到家,陈砚墨把自己关在屋里,
对着《农村养殖手册》反复盘算。
突然,他想起村里的老会计家有闲置的谷仓,
或许可以先租下来当临时猪圈。
正想着,外头传来争吵声。
“你疯了!拿全家的口粮钱去赌?” 是父亲的怒吼。
陈砚墨冲出门,见父亲正将母亲手里的布包夺过来,
里面露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原来母亲偷偷攒了些钱,想支持儿子的计划。
“爹,我算过了,租老会计家的谷仓,先养五头猪试试...”
陈砚墨话没说完,父亲抄起墙角的竹扫帚,
“啪” 地打在木桌上,震得碗柜里的粗瓷碗叮当作响:
“家里的米缸见底了,你还做梦!”
“五头猪每天要吃多少?拿西北风喂?”
母亲突然抓住父亲的手腕,声音发颤:
“他爹,租别人的终归不好。”
“我寻思着,要是能咬牙把谷仓买下来,这样自己的才踏实。”
“不然以后砚墨养猪赚钱了,人家要收回谷仓,不租了,咱可就太被动了。”
她转头望向陈砚墨,目光里满是坚定,“我们凑凑看...”
父亲的喉结上下滚动,竹扫帚 “当啷” 落地。
陈砚墨望着父母鬓角的白发,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夜风卷着几片枯叶从敞开的院门飘进来,在地上打着转。
母亲还保持着伸手阻拦的姿势,手指微微颤抖;
父亲背过身去,佝偻的脊背在月光下像一张拉满的旧弓。
“先... 先攒点钱吧。”
陈砚墨蹲下身,捡起地上散落的钞票,粗糙的毛边硌得掌心生疼,
“买猪仔、租谷仓都要钱,咱们不能把口粮钱全搭进去。”
他声音发闷,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
母亲张了张嘴,终究没说话,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突然听见西屋传来争吵声。
推开门,就见奶奶举着竹竿要打陈砚韬:
“小兔崽子偷翻柜子!”
小红躲在爷爷身后,指着地上散落的邮票:
“他抢我的宝贝!”
陈砚韬的手背被竹竿抽得通红,却死死护着怀里的旧课本:
“我没偷!是这邮票夹在书里!”
陈砚墨冲过去挡在弟弟身前,捡起邮票却愣住了 ——
泛黄的纸面上印着 1980 年庚申猴票。
他在现代曾听说单张价值上万,而眼前足足十张。
奶奶见状突然换了副嘴脸: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这邮票就当补贴家用,明儿让国强拿去县城卖。”
“不行!”
陈砚墨将邮票塞进弟弟书包,
“这是三弟先发现的,该由他决定。”
月光下,陈砚韬打开课本,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 “给大哥买计算器”。
陈砚墨喉咙发紧,转头对父母说:
“我想好了,明天就去县城找门路,这鱼我们要往城里餐馆送,邮票... 也该找专业的人鉴定。”
此时,漏雨的茅草屋又开始滴答作响,但陈砚墨望着夜空闪烁的星子,握紧了弟弟的手。
第二日天还未亮,陈砚墨揣着两张猴票,带着三弟踏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
破旧的客车颠簸在土路上,扬起阵阵灰尘,三弟陈砚韬攥着车票,紧张得手心冒汗:
“哥,这邮票... 真能值很多钱?”
陈砚墨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脑海中闪过奶奶昨晚阴鸷的眼神,点头道:
“等鉴定完就知道了。”
县城的邮票市场藏在一条老巷子里,七拐八绕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家挂着 “集邮斋” 招牌的小店。
店主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接过邮票时,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异样的光。
“二位运气不错,” 他推了推眼镜,
“不过庚申猴票赝品太多,我得仔细瞧瞧。”
说着,转身进了里屋。
半小时后,店主出来时面色凝重:“可惜了,这是仿品,不值钱。”
陈砚墨心猛地一沉,却瞥见店主袖口里露出一角熟悉的泛黄纸张 —— 正是自己带来的邮票。
还未等陈砚墨开口,店主突然换了副语气,从抽屉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不过我看你们是老实人,这仿品做得倒也精巧,我出两百块收了,就当交个朋友。”
陈砚墨不动声色地拉过三弟,想起在现代听闻过的邮票炒作新闻,心里己然明白这邮票的巨大潜力。
他强压下怒火,笑道:
“既然是假的,那就当留个纪念。”
出了店门,陈砚墨着邮票边角,
暗自决定将这些邮票好好收藏,等待日后价值飞涨。
走在县城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他路过一家邮票店。
橱窗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邮票,一张庚申猴票的宣传海报格外醒目。
他驻足良久,心里盘算着:
要是咬咬牙,把家里能凑的钱都拿来买 20 张庚申猴票。
等过些年增值了,家里的困境就能彻底解决。
可转念一想,母亲为了支持自己的计划,
偷偷攒下的钱差点被父亲全部否定;
家里的米缸早己见底,鱼生意刚刚有了一点眉目,
后续扩大规模、养猪计划的推进都需要大量资金。
“还是把钱留在手里,有流动资金比较好一点。”
陈砚墨喃喃自语,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一点余钱,转身离开了邮票店。
他知道,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家庭现状下,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让家人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另一边,陈砚朗在家也没闲着。
他按照陈砚墨的嘱咐,挨家挨户走访镇上的餐馆。
在被拒绝七次后,终于在一家新开的川菜馆遇到了转机。
老板王建国尝了陈砚朗带来的鲜鱼后,眼睛一亮:
“这鱼够新鲜!”
“但丑话说在前头,我每天要三十斤,价格得按批发价算。”
陈砚墨回来后,拍板答应了王老板的条件。
“两块一斤就两块!”
他盯着合同上的数字,指节捏得发白,
“但王老板,咱们丑话说在前头,鱼的品质您放心,可这货款得隔天结清。”
王建国叼着烟点点头,在合同上龙飞凤舞地签了字。
消息传回家里,父亲蹲在门槛上闷头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一斤鱼才卖两块?”
母亲顿了顿:
“要不咱再和王老板谈谈?”
陈砚墨望着墙上漏雨的水渍,声音却斩钉截铁:
“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开销路,等咱们稳住了,价格自然能涨。”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破旧的窗棂洒进院子。
二弟陈砚朗背着满满一背篼猪草回来,
汗水浸透了洗得发白的短袖,草叶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哥,我把村西头坡上的猪草割了些,”
他放下背篼,抹了把脸上的汗,
“那片草长得旺,再长些时日,怕是要把路都盖住了。”
陈砚墨望着鲜嫩的猪草,心中一动。
虽然养猪计划暂时搁置,
但这些猪草却像是提前埋下的希望种子。
三弟陈砚韬则捧着从学校借来的书,坐在门槛上看得入神。
书页被风吹得轻轻翻动,他时不时用铅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哥,我在书上看到有种新型的鱼饲料配方,”
他突然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
“要是能试一下,说不定鱼长得更快!”
陈砚墨走过去,揉了揉弟弟的头,
少年的想法或许稚嫩,却像一束光照进他满是压力的心里。
厨房里,母亲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火苗 “噼啪” 窜起。
陈砚墨蹲在一旁帮忙择菜,看着母亲布满老茧的手熟练地切着野菜。
“娘,等鱼生意稳定些,我想雇几个人一起捕鱼,”
他低声说,“您和爹就不用这么累了。”
母亲动作顿了顿,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笑意:
“只要你们兄弟有出息,娘再累也值得。”
院子另一角,父亲戴着老花镜,正专注地编着竹席。
竹篾在他指间穿梭,发出有节奏的 “沙沙” 声。
陈砚墨走过去时,正看见父亲将断裂的竹篾挑出来,眉头皱成个 “川” 字。
“这根篾太脆,编进去要露破绽。”
父亲头也不抬,“做买卖和编竹席一个理,掺不得半点假。”
这话像是说给竹席听,又像是在叮嘱儿子。
暮色渐浓,油灯亮起,昏黄的光晕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
粗瓷碗里装着野菜粥,虽然清淡,却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陈砚墨望着身边的亲人,想起白天在县城的抉择,
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
不管前路多艰难,他都要带着家人。
从这一背篼猪草、一本旧书、一张竹席开始,
蹚出一条属于他们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