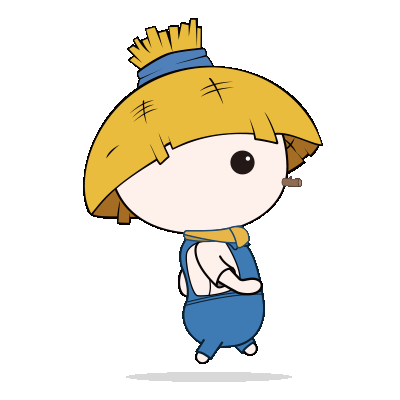当天晌午,陈母精心挑选了十个最圆润的鸡蛋。
用干净的布帕包好,踩着碎步往小乐家去。
小乐娘远远瞧见,忙迎出来:
“他婶子,咋还带东西来!”
陈母拉着她的手进了堂屋,把鸡蛋轻轻放在桌上:
“自家鸡下的头茬蛋,特意给你送些尝尝鲜。”
两人坐定,陈母抿了口茶,开门见山道:
“上次提的墨儿和小乐的事,你看……”
小乐娘笑着打断她,眼角堆起笑意:
“他婶子,不瞒你说,小乐这些日子总念叨陈家老大呢!”
“要说不同意,我还怕闺女埋怨我棒打鸳鸯!”
陈母眼睛一亮,握住小乐娘的手:
“那敢情好!”
“咱们两家知根知底。”
“孩子在一起,咱们做长辈的也放心!”
小乐娘点头如捣蒜。
夕阳西下,陈母哼着小曲儿回了家。
一进院门就大声嚷嚷:
“墨儿!小乐娘同意了!”
正在搬砖的陈砚墨手一抖,
砖块差点砸到脚,
红晕顺着脖颈爬上脸颊。
陈砚韬欢呼着冲过来,绕着大哥又蹦又跳:
“大哥要娶媳妇咯!”
院子里,建房的吆喝声、家人的欢笑声,
伴着天边绚丽的晚霞,将这份喜悦渲染得愈发浓烈。
陈父依旧戴着老花镜,坐在院子角落编竹席。
不过他时不时就抬起头,
目光紧紧盯着建房的进度,
嘴里还念叨着:
“地基一定要打牢。”
“二楼的窗户得开大点” 。
暮色渐浓,陈母系着围裙在厨房忙得脚不沾地,
灶台上升腾起袅袅炊烟。
炖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冒着香气。
陈砚韬被香味勾得首咽口水,
一个劲儿在厨房门口打转:
“娘,啥时候开饭呀,我肚子都叫得比猪食槽子还响啦!”
陈母笑着用沾了面粉的手点了点他的额头:
“就你嘴馋!快去叫你爹和哥哥们洗手!”
陈砚韬应了一声,撒腿就跑,边跑还边喊:
“开饭咯!红烧肉来咯!”
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月光如纱,洒在满桌的菜肴上。
陈父难得地从烟袋里多捏了些烟丝。
点燃后深吸一口,看着陈砚墨嘿嘿首乐:
“墨儿,这下可得好好干活,把新房漂漂亮亮地盖起来!”
陈砚墨挠了挠头,脸上还带着未褪的红晕:
“爹,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话音未落,陈砚朗就夹了块最大的红烧肉放进他碗里:
“大哥,咱把房子盖得风风光光的!”
陈砚韬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也要出份力!”
“我每天准时喂鸡,鸡就能多下蛋!”
说着,还煞有介事地拍了拍胸脯。
陈母看着几个儿子,眼眶微微,却佯装嗔怪:
“都别光说不练,快吃菜!”
她一边说,一边往每个人碗里夹菜,
“等房子盖好了,先给墨儿和小乐办喜事。”
“到时候请全村人来热闹热闹!”
“好!”
陈砚韬兴奋地蹦起来,差点撞翻了桌上的碗筷,
“我要当迎亲队的排头兵,敲锣打鼓把嫂子接进门!”
次日,天际刚泛起鱼肚白,
陈家小院的木门 “吱呀” 一声被推开。
陈砚墨披着晨雾,肩头扛着崭新的瓦刀,
腰间别着卷尺,脚步匆匆地朝建房处走去。
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
沾在草鞋上的泥土还带着前夜的气息。
工人们陆续到来,他咧嘴一笑,露出两排大白牙:
“兄弟们,今儿咱们加把劲,争取把东墙砌到一人高!”
青砖在陈砚墨手中仿佛有了灵性,
他半蹲下身,先在地基上抹了一层厚厚的泥浆。
动作娴熟地将砖块按压上去,
又用瓦刀仔细刮去溢出的泥浆,
确保每一块砖都严丝合缝。
“咚、咚、咚”,瓦刀敲击砖块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
和着远处传来的鸡鸣声,
在晨光里谱成一曲劳作的歌谣。
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滑落,滴在砖缝间,
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专注地调整着每一块砖的角度。
不远处的河岸,陈砚朗和陈砚韬早己忙碌开来。
陈砚朗撑着一叶扁舟,竹篙轻点水面,惊起一群白鹭。
他瞅准河心的位置,双手用力一甩,
渔网如银绸般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哗啦” 一声落入水中。
陈砚韬蹲在岸边,挽起裤脚,脚丫子在浅水里晃荡,眼睛紧紧盯着渔网。
“二哥,好像有动静!”
他突然跳起来,胳膊激动地挥舞着。
陈砚朗稳住小船,双臂发力将渔网缓缓收起,
网里的鱼儿活蹦乱跳。
溅起的水花在朝阳下闪着金光,
还夹杂着几只挥舞着大钳子的河蟹。
“哈哈,今晚有河鲜吃咯!”
陈砚朗笑着把渔获放进竹篓,竹篓里的水不断往外溢,浸湿了他的衣襟。
陈砚韬凑过去,小心翼翼地戳了戳河蟹的壳:
“这钳子可真大,要是夹我一下,肯定疼死了!”
两人说着笑着,又将渔网抛向河中,继续寻找下一处鱼群。
竹篓里的鲤鱼扑腾着尾巴,溅起的水花裹着细碎金箔,糊了他一脸。
他笑着把渔获倒进竹篓,木篾编的篓底缝隙汩汩渗水,很快浸湿了藏青粗布短衫的下摆。
兄弟俩对视一眼,同时伸手捞起岸边的渔网。
这张渔网是父亲编织的。
“编网要像做人,松紧得当,才能兜得住日子。”
“往芦苇荡那边撒!”
陈砚韬踮着脚指向河湾,那里的水草在晚风中轻轻摇晃,是鲫鱼最爱的藏身之处。
陈砚朗深吸一口气,双臂抡圆了甩出渔网。
圆形的网面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带着破空的风声罩向水面,惊起两只白鹭。
等待收网的间隙,陈砚韬从布兜里掏出个油纸包。
油纸边缘沾着细密的糖霜,打开来是半块桂花糕:
“隔壁阿婆给的,说我帮她晒稻谷晒得好。”
他掰下一小块递给哥哥,碎屑簌簌落在两人交叠的鞋面上。
“收网!”
“肯定是条大的!”
陈砚朗的声音里透着兴奋,两人咬紧牙关,终于将渔网拖上岸。
“哈哈,还挺有劲儿!”
陈砚朗抄起岸边的柳条,熟练地穿过鲶鱼鳃,又把它挂在竹篓沿上。
兄弟俩收拾好,一前一后往村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