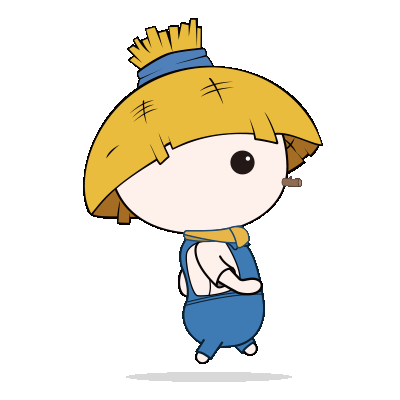新政学堂一千二百名学子领命赴任、崇祯密令锦衣卫暗中关注处...
初春的寒气还在肆虐,通往河南归德府永城县的官道上,扬起漫天尘烟。几辆破旧的骡车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艰难颠簸,车上堆满简单的行囊,还有几口沉重的木箱。新任永城知县刘定边,身着洗得发白的青色襕衫,外面罩着一件旧棉袍抵御寒风,他眉头紧皱,目光凝重地望着前路。与他同行的,只有从南京带来的两名新政学堂出身的书吏,以及兵部临时调拨的十名老弱护卫,这些人脸上都写满了风霜。
越靠近永城,眼前的景象愈发凄惨。大片田地荒芜,村落残破不堪,焦黑的断壁残垣无声诉说着不久前闯军过境的惨烈。流民蜷缩在路旁废弃的窝棚里,眼神空洞麻木,不时能看到倒毙路旁的尸体,引得成群的乌鸦聒噪盘旋。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气息。
“大人,前面就是永城县城了。”书吏王茂才指着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低矮城墙,声音里满是忧虑。
刘定边轻轻点头,脸上没有半点新官上任的喜悦。他心里清楚,永城的局势极为棘手:城池两个月前才从闯军刘体纯部手中收复,前任知县和大部分吏员非死即逃,县衙几乎被烧成了废墟。城内粮仓空空如也,城外流民越聚越多,整个县城秩序全无。更麻烦的是,听说左良玉部卢光祖的兵马就在邻县活动,像恶狼一样盯着这里。
队伍刚走到残破的南门外,就被一群衣衫褴褛、手持简陋棍棒的民壮拦住了去路。为首的疤脸汉子警惕地打量着他们:“站住!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护卫队长上前交涉:“别放肆!这是朝廷新任命的永城县令,刘定边刘大人!还不赶紧让路!”
“县太爷?”疤脸汉子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很快又被更深的戒备取代,“空口无凭!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左军假扮的?或者是闯贼的探子?前几天就有一伙人打着官府旗号想进城抢粮!”他身后的民壮们也纷纷握紧手中的棍棒,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护卫们下意识地按住了腰刀。
刘定边见状,示意护卫退下,自己走上前,掏出吏部官凭印信,大声说道:“我是刘定边,奉天子诏命、吏部行文,特来永城担任知县。这是官凭印信,你们查验一下。”他语气平和,没有一点官架子。
疤脸汉子狐疑地接过官凭,他识字不多,翻来覆去看不太明白。旁边一位略通文墨的老者凑过来仔细辨认,又查看了印信,这才颤抖着声音说:“张头儿…是真的,有吏部大印,还有…还有陛下的玉玺…这位真是朝廷派来的青天大老爷!”
疤脸汉子张头儿听了,神色稍微缓和,但还是保持着警惕:“大人…不是我们不信,实在是被折腾怕了!闯贼抢,左兵也抢,城里就剩这点救命的粮食种子,真经不起折腾了!大人要是真来救永城,带粮食了吗?”他眼神里满是期待,也带着最后的试探。
刘定边心里一阵酸楚,摇摇头坦诚地说:“我这次轻车简从,只带了朝廷给的一点盘缠,没带粮食。不过朝廷己经知道永城的难处,筹措的粮草正在运来!我在此发誓,进城第一件事,就是清点粮仓存粮,登记城中人口,按户按人公平分配!绝不让一粒救命粮被抢走!要是违背誓言,就让老天惩罚我!”
他这番坦诚的话和坚定的誓言,让张头儿和民壮们眼中的敌意消去大半。张头儿犹豫了一下,一挥手:“开城门!请…请县尊大人进城!”
与此同时,在江南常州府无锡县,新任劝农使陈耕野的赴任之路,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无锡县衙后堂,窗明几净。陈耕野,这个皮肤黝黑、双手布满老茧的前松江府农人,此刻穿着崭新的青色官袍,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面前,堆满了前任留下的所谓“鱼鳞图册”和历年钱粮账簿,墨迹陈旧,字迹潦草模糊。县丞孙德海,一个胖乎乎、总是笑呵呵的中年人,正满脸殷勤地向他介绍:
“陈大人一路辛苦了!无锡可是鱼米之乡,农桑之事向来安稳。这是本县历年田亩图册,这是去年秋粮征收的底档…对了,这是本县几位德高望重的粮长、里老名录,大人以后推行新政,少不了要靠他们帮忙。”孙德海语气恭敬,脸上堆满笑容,可眼神却时不时扫过陈耕野翻看账簿时皱起的眉头。
陈耕野翻看着那些图册,心里越来越沉重。图册上记载的田亩数量,和他一路所见,还有新政学堂教的“步弓丈量法”估算的结果相差甚远!很多肥沃的田地被标成“下田”或“荒地”,反倒是一些贫瘠的山坡成了“上田”。账簿上的数字更是乱成一团,征收、存留、损耗、摊派…各种条目密密麻麻,让人看得头晕。
“孙县丞,”陈耕野放下账簿,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我看这些图册,好像和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新政最要紧的就是清丈田亩,保证税赋公平。我想选几个里甲,先重新丈量,做个示范,你觉得怎么样?”
孙德海脸上的笑容微微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哎呀,陈大人新官上任,干劲十足,下官佩服!不过…这清丈田亩,牵扯的人和事太多,又费人力又费物力。现在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要是大张旗鼓地去做,恐怕会打扰百姓,耽误农时。而且…”他压低声音,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这里的豪绅大户,势力盘根错节。前任也不是不想清丈,可阻力太大,稍微不小心惹出乱子…那就麻烦大了。下官觉得,不如先熟悉熟悉情况,以后再慢慢打算?”
陈耕野心里冷笑,这“徐徐图之”西个字,就是那些旧官吏拖延、阻挠新法的惯用手段!他想起学堂里李侍郎的教诲:遇到阻挠,就要用律令当武器,按实际情况弹劾!于是他严肃地说:“孙县丞这话不对!清丈田亩、厘清税基,是朝廷新政的铁律,也是解救百姓的根本!农时虽然重要,可赋税不公平,百姓怎么能安心?我主意己定,明天就挑选吏员,跟我去东亭乡重新丈量!需要的步弓、算吏,你马上准备!”
孙德海眼底闪过一丝不悦,脸上却还挂着笑:“是是是,大人雷厉风行,下官佩服!我这就去准备!”他躬身退下,一转身,脸上那恭敬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浙江杭州府钱塘县衙,新任知县周维新正面临一场无声的“账簿之战”。
宽敞明亮的二堂内,新任户房司吏孙算盘(原是扬州盐商的账房先生),带着两名同样精通新式复式记账法的书吏,埋头在堆积如山的历年钱粮簿册中。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就像密集的雨点。
周维新端坐在案后,面色沉稳,眼神却锐利如鹰。他面前站着钱塘县原户房典吏赵有财,一个白白胖胖、眼神躲躲闪闪的中年人。
“赵典吏,”周维新声音不高,却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威压,“我查阅了天启七年到崇祯十年的漕粮折色银账目,发现很多可疑的地方。第一,折色银兑换比率,朝廷明明规定每石米折银七钱,可县里的账目记载,这些年兑换比率浮动很大,从六钱五分涨到八钱,还没有朝廷的批文。第二,损耗这一项,每年都超过两成,比户部规定的一成多太多。第三,解送到藩库的银两数目,和县里存留、开销的总数对不上,差额加起来超过一万两。这些出入,你怎么解释?”
赵有财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强装镇定地说:“回…回禀县尊,折色兑换比率,因为每年米价不一样,所以会有浮动,这是惯例…损耗…损耗是因为路途太远,仓库保管不好,还有老鼠、麻雀偷吃…至于差额…可能是…可能是历年交接,账册抄写的时候偶尔弄错,积少成多…下官…下官马上带人重新核对…”
“弄错?”周维新拿起一本账簿,指着一处墨迹明显不同的涂改痕迹,“这笔崇祯八年的折色银收入,原来记的是一千五百两,改成了一千两。这处墨迹比旁边的新,明显是后来改的!这也算弄错?”他重重地把账簿拍在桌子上!
赵有财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脸色惨白:“大人…大人明察!这…这肯定是前任书吏糊涂…下官…下官真的不知道啊!”
周维新冷冷地看着他:“不知道?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天启七年到现在所有的原始凭证、流水底单都整理好,和我带来的新式账册一项一项核对!凡是有涂改、缺漏、对不上账的地方,让户房所有经手的吏员签字画押,写清楚原因!要是再敢隐瞒、糊弄…”他顿了顿,声音冰冷刺骨,“别怪我不客气,按照新颁布的《官吏惩戒则例》,从严惩处!退下!”
赵有财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后背的官袍己经被冷汗湿透。
周维新看向孙算盘:“情况怎么样?”
孙算盘抬起头,眼神发亮:“大人,旧账乱得一塌糊涂,到处都是漏洞,短时间内根本查不清楚。不过他们的手段,无非就是‘飞洒’(把田赋转嫁到小户头上)、‘诡寄’(把田地假报到不用交税服役的名下)、‘虚报损耗’、‘篡改兑换比率’这几种。有了新政的记账方法,再加上追查原始凭证,只要给点时间,肯定能把真相查清楚,追回赃款!”
“好!”周维新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就从钱塘县开始,让那些蛀虫知道,朝廷的新政,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镇江府丹徒县,主簿李振声刚到任,就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他在破旧的县衙主簿廨还没安顿好,连官服都没来得及换,县衙外就传来一阵震天的喧哗和哭喊声。紧接着,一名浑身湿透、满脸惊恐的差役撞开房门:“李…李主簿!不好了!运河…运河丹徒段新修的河堤塌了!淹了…淹了下游三个村子!”
李振声脑袋“嗡”的一声,猛地站起身:“什么?!快带我去!”
他骑马赶到溃堤的地方,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浑浊的运河水从一道十多丈宽的决口汹涌而出,大片农田和村舍都被淹没。无数百姓在齐腰深的水里哭喊着,拼命抢救家里的东西和牲畜。倒塌的房屋只露出半截屋顶在水面上。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绝望的气息。
“李主簿,您可算来了!”负责这段河工的工房典吏钱贵哭丧着脸跑过来,“这…这可怎么办啊!这河堤…这河堤上个月刚按府里要求加高加固过!花了…花了好大一笔银子,怎么就…怎么就塌了!”
李振声没理他的哭诉,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和愤怒,厉声问道:“马上组织人堵决口!县里常备的防汛物资呢?麻袋、木桩、草捆?民壮都在哪儿?”
钱贵支支吾吾:“物…物资…仓库里还有一些,可…可恐怕不够…民壮…民壮都在地里忙春耕,一时半会儿…”
“胡说!”李振声怒喝一声,新政学堂培养出来的果敢劲儿一下子显现出来,“春耕再重要,能比人命还重要?!传我的命令:第一,立刻打开县仓,把所有装粮的布袋都装上沙土运过来!不够就拆门板、卸房梁!第二,让巡检司拿着我的令牌,敲锣召集百姓!下游所有村庄,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丁,马上带着工具来堵决口!谁敢违抗,就按贻误河工、危害乡里论处!第三,让医官赶紧准备金疮药、姜汤,救治落水的百姓!第西,工房所有人,马上给我彻查!这河堤到底为什么会塌!用料、做工、监管情况,一样都别漏!快去!”
他雷厉风行的命令,暂时稳住了混乱的局面。差役们飞奔而去执行命令。李振声看着汹涌的洪水,又看了看钱贵那张惊慌却难掩心虚的脸,心里明白:这突然的溃堤,恐怕没那么简单!他握紧拳头,新政推行的第一道难关,竟然如此残酷。他深吸一口气,大步走向泥泞的河堤,在混乱的人群中,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坚定。朝廷的新政,能否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站稳脚跟,这场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