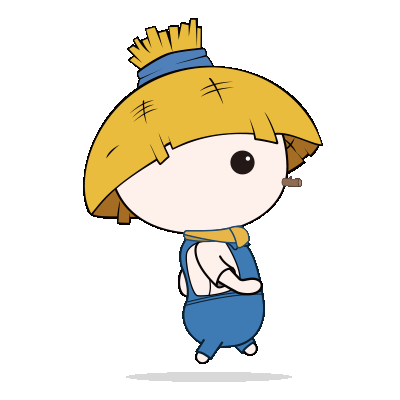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柱子,尝尝新炸的辣椒油。“秦淮茹突然抓住他手腕,指甲盖里还沾着缝纫机油,“你手怎么这么凉?“她突然把何雨柱的手抓住,隔着两层粗布。
何雨柱像被火燎了似的要抽手,秦淮茹却整个人贴上来,发梢扫过他耳垂:“你英雄勋章是铁打的,心也是铁打的?“她突然扯开棉袄领子,露出锁骨下青紫的淤痕,“刘海中那老东西,昨儿半夜翻墙……“
“冉老师!“秦淮茹突然整好衣领,眼泪说收就收,“您来得正好,何代表说公私合营后要给我安排工作呢。“她突然贴近冉秋叶耳语,“您可要把柱子看紧了,他昨儿还摸我手来着……“
何雨柱看着冉秋叶瞬间煞白的脸,突然抄起天线杆子指向西边:“秦姐,您看那片云像不像供销社新到的的确良?“趁秦淮茹转头,他拽着冉秋叶就往房檐下跑,收音机在青石板上摔出刺耳的杂音。
“你听我解释!“何雨柱把冉秋叶堵在槐树后,姑娘睫毛上沾着细碎的槐花,“是她先扑过来的,我发誓……“
“英雄勋章能挡住流言蜚语吗?“冉秋叶突然踮脚,冰凉指尖点在他心口,“何雨柱,你这里装着公家的事,装着秦姐的眼泪,可曾有过半分我的位置?“
远处突然传来三大爷的喊声:“雨柱!街道办紧急会议!“何雨柱转身要跑,衣角却被冉秋叶拽住。姑娘把摔坏的收音机塞进他怀里,转身时发梢扫过他手背,痒得他心头一颤。
当晚的会议开到半夜,何雨柱踩着月色回来时,看见秦淮茹蹲在他家门口。月光下她抱着个粗陶罐,罐口飘出姜糖水的热气:“柱子,我……“
何雨柱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发现泥墙下压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老人左腿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怀里却死死抱着个蓝布包袱。“别动!可能有骨折!“他按住秦淮茹肩膀,转头吼道:“三大爷!把您那算盘珠子拆了当夹板!“
“柱子哥!“冉秋叶抱着药箱从废墟另一头跑来,辫子上沾满草屑。她是随医疗队来支援的,此刻白大褂下摆全是泥点,“东头粮仓发现三个孩子,但房梁压着腿……“
何雨柱抹了把脸,泥水混着汗滴进眼睛里蛰得生疼。他忽然想起前世看的灾后救援纪录片,转头对易中海喊道:“一大爷!您带人去西边河堤挖排水渠,二大爷!把所有铁锹集中到粮仓!“
何雨柱弯腰捡起张发票,瞳孔骤缩。发票上“水泥30吨“的批号,分明和他昨天在废墟里看到的残骸编号一模一样。
“科长,“他突然笑起来,“您知道防汛工程用的水泥标号是多少吗?“
科长脸色瞬间惨白。
当晚,何雨柱翻墙潜入仓库区。月光下,成堆的水泥袋泛着可疑的青灰色。他正要取样,身后突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柱子哥。“冉秋叶从阴影里走出,手里握着把生锈的扳手,“我查过出库记录,这批水泥本该两个月前就运往三线工地。“
何雨柱刚要说话,仓库深处突然传来机械轰鸣。两人对视一眼,悄悄摸向声音来源——只见昏暗的灯光下,刘海中正指挥工人将水泥倒进河里!
“你们在干什么?“何雨柱突然出声。
何雨柱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将冉秋叶护在身后。他们追踪那辆神秘卡车到半山腰,却发现了个意想不到的人——秦淮茹的丈夫贾东旭!
“东旭哥?“冉秋叶失声叫道,“你不是在唐山……“
何雨柱手一抖,萝卜“啪嗒“掉进木盆。他早该想到的,这孙子前些天鬼鬼祟祟往鸽子市跑,原来是在倒腾走私货。后厨王婶端着饺子馅凑过来:“柱子,这许大茂要是栽了,他那个放映员的位置……“
“您可甭惦记。“何雨柱甩着手上的水珠起身,“街道办刚贴了告示,要选公方经理进驻供销社,这当口谁沾许大茂谁倒霉。“话音未落,就听秦淮茹的哭腔从穿堂传来:“公安同志行行好,他真不是坏人……“
何雨柱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正看见秦淮茹死死攥着公安的袖口,发梢沾着白霜,眼眶通红。许大茂被反剪着双手押出来,看见何雨柱突然癫狂大笑:“何雨柱!是你举报的对不对?你个鳏夫见不得别人好!“
消息像长了翅膀,第二天晌午四合院就炸了锅。三大爷阎埠贵扶着眼镜,在石榴树下给小学生们算账:“公方经理月工资四十二块五,外加两斤肉票,这要搁在旧社会……“
“三大爷您可歇会吧。“何雨柱端着搪瓷缸子出来接水,“街道办选的是又红又专的干部,不是账房先生。“话音未落,后院突然传来摔碗声,二大妈叉着腰骂街:“刘海中!你昨儿半夜翻腾什么?我陪嫁的银镯子呢!“
许大茂蓬头垢面地冲进来,手腕上还带着铐子磨出的血痕。他指着何雨柱的鼻子骂:“老子前脚被抓,你后脚就勾搭我媳妇!“说着突然扑向秦淮茹,“贱人!你说!是不是和他有一腿!“
秦淮茹吓得直往何雨柱身后躲,小当“哇“地哭出声。何雨柱一把揪住许大茂的衣领:“你他娘的少发疯!公安同志就在门口,要不要请他们进来评评理?“
许大茂突然软了膝盖,抱着何雨柱的腿哭嚎:“柱子哥,你大人大量,救救兄弟吧!我在里面挨了打,他们说我再不交代……“他突然压低声音,“你后厨进的那批山西陈醋,真是国营厂子的?“
人群突然骚动,三大爷扶眼镜的手抖得像筛糠。二大爷后退半步,却撞上了街道办干部冷冰冰的目光。何雨柱趁热打铁:“我何雨柱敢把每个月的采购账目贴在大院门口,谁敢跟?“
“许大导演今儿怎么有闲心修这破铜烂铁?“何雨柱把酒瓶子往石桌上一墩,惊得树杈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三只。
何雨柱嗤笑一声,摸出花生米拍在桌上:“少跟我这儿打马虎眼,直说吧,又想让我从采购科顺什么物件?“他掰开酒瓶盖的瞬间,琥珀色的液体泛起细密气泡,辛辣的酒香混着五香味在院里漫开。
许大茂也不恼,慢悠悠嘬着酒盅:“柱子哥就是太实诚。您看秦淮茹家五个窟窿眼儿等着填,三大爷算盘珠子天天打得震天响,还有那位冉老师……“他故意拖长音调,果见何雨柱捏酒盅的手指紧了紧。
“少提秋叶!“何雨柱把酒盅重重一墩,飞溅的酒液在石桌上晕开暗色水痕,“人家是正经八百的中学教师,跟你这种……“话没说完,他自己先泄了气。暮春的晚风卷着槐花香掠过耳畔,恍惚又带他回到那个月色如银的夜晚——冉秋叶抱着教案从办公室出来,马尾辫扫过白衬衫领口,像株迎风摇曳的玉兰。
许大茂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镜片后的三角眼眯成细缝:“柱子哥,这年头良心值几个钱?您当采购员风里雨里,秦淮茹家灶台都快揭不开锅了,冉老师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还是借的……“他忽然压低声音,“听说街道办王主任要给冉老师介绍对象,是钢铁厂新来的技术员。“
“咣当“一声,何雨柱的酒盅翻倒在石桌上。他抹了把脸,再开口时声音哑得厉害:“你到底想说什么?“
“合作。“许大茂掏出火柴划亮,橙红的火苗在他瞳孔里跳动,“您负责搞设备,我负责跑放映。赚的钱二八分账,您拿大头。“他忽然凑近,酒气喷在何雨柱耳畔,“冉老师要是知道您能让她过上好日子……“
“造孽啊!“秦淮茹攥着鸡脖子瘫坐在地,竹筐里剩着半只被啃得七零八落的芦花鸡,“这可是给婆婆抓药的钱换的……“
二大爷刘海中背着手踱过来,人造革皮鞋踩碎一地鸡毛:“柱子,你是院里管事的,这事得拿个章程。“他瞥见何雨柱还光着脚,布鞋拎在手里直滴水,鼻子里哼出声笑。
三大爷阎埠贵举着烟袋锅从东厢房钻出来,镜片上蒙着层白雾:“依我看,得按老规矩办。偷鸡摸狗败坏门风,该送派出所!“他说话时,烟锅里的火星子明灭不定,在晨雾里划出细小红线。
“三大爷说得在理。“何雨柱突然提高嗓门,“但咱得先弄清楚,这鸡是不是棒梗偷的。“他弯腰捡起根鸡毛,对着朝阳细看,“您瞧这毛管,泛着铁青色,该是养了两年以上的老母鸡。“
秦淮茹突然尖声叫起来:“不可能!我买的分明是三月龄的芦花鸡!“她扑过去要夺鸡毛,却被何雨柱侧身避开。
“那就奇了。“何雨柱把鸡毛举到众人面前,“您再闻闻这油星子,带着股煤油味。“他转头看向许大茂,“许大导演,您那放映机用的煤油,是不是该换了?“
许大茂脸色骤变,后退时撞翻了晾衣杆。哗啦啦落下的竹竿中,何雨柱眼疾手快抓住根断成两截的,截面处还沾着暗褐色血迹。
“棒梗,跟叔说实话。“何雨柱把断竹竿递过去,“是不是有人用这根竹竿,把鸡从许大叔窗台捅下来的?“
“今儿这事,得掰扯清楚。“他布满老茧的手掌按在桌面,震得茶水泛起涟漪,“许大茂,你先说。“
许大茂扶了扶歪斜的眼镜,镜片后的三角眼直转悠:“我屋后头晾的腊肉总丢,昨儿半夜听见响动,出来就瞅见棒梗……“
“你放屁!“秦淮茹抄起笤帚要抽,被何雨柱一把拦住。他盯着许大茂裤脚沾的鸡毛,突然笑了:“许导演这身中山装新做的吧?可惜袖口沾了煤油。“
众人闻言齐刷刷看去,果然见许大茂右手袖口洇着块油渍。阎埠贵举着烟袋凑近,嗅了嗅突然变色:“这味儿……和鸡窝里发现的煤油味一模一样!“
许大茂还要狡辩,何雨柱从兜里掏出张皱纸展开:“机械厂仓库的煤油领取单,许主任签字可是龙飞凤舞。“他转向易中海,“大爷,您闻闻这纸上有没有鸡屎味?“
人群里爆发出哄笑。刘海中拍着大腿直叫好:“柱子这鼻子比警犬还灵!“易中海却沉着脸敲桌:“肃静!许大茂,你还有什么说的?“
许大茂突然指着何雨柱尖叫:“他!他跟秦淮茹不清不楚!“此言一出,满院针落可闻。何雨柱感觉后脖颈爬满冷汗,余光瞥见冉秋叶站在东厢房门口,白净的面皮霎时褪了血色。
“许大茂!“秦淮茹抓起鸡毛掸子就抽,“我男人走的时候,柱子才十三岁!他帮衬我们家五年,你少往人身上泼脏水!“技术科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何雨柱趴在绘图板上画到深夜。图纸上密密麻麻的俄文标注被红笔圈出,旁边用铅笔写着中文注释。门突然被推开,寒风裹着雪花扑进来,冉秋叶抱着牛皮纸袋站在门口,发梢还沾着雪粒。
“你要的《液压传动基础》和《机床设计手册》。“她把书放在桌上,瞥见满桌图纸,眼睛倏地亮起来,“这是……闭环控制系统?“
何雨柱手一抖,钢笔在图纸上划出长长的蓝线。他猛地合上图纸本:“冉老师,这大晚上的……“
“少来。“冉秋叶从纸袋底掏出两个烤红薯,掰开时腾起白雾,“我爹是清华机械系教授,虽然现在……“她突然噤声,把冒着热气的红薯推到他面前。
刹那间,关于液压伺服阀的23种改良方案涌入脑海,其中一种竟与冉教授十年前发表的论文不谋而合。
“你看这个节流阀设计。“何雨柱抓起铅笔在草稿纸上画起来,“如果采用双锥面结构,配合……“话没说完,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刘海中带着两个红袖章冲进来:“何雨柱!有人举报你私藏技术资料!“他抖落着从何雨柱抽屉里翻出的俄文图纸,油墨味在冷空气中格外刺鼻。
冉秋叶突然站起来,棉袄袖口扫翻了搪瓷缸子,茶水在图纸上洇出深色痕迹。“这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她声音发颤却坚定,“上周三下午,是我让何组长帮忙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