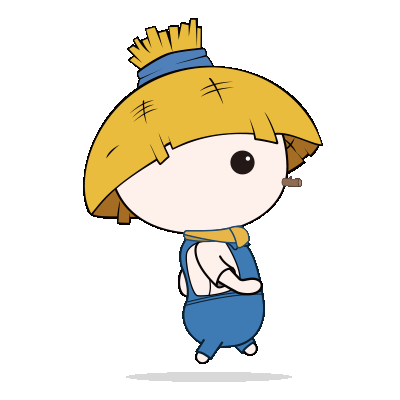肉做的鲸能轻松下潜2000米,为何钢铁之躯的潜艇却不行?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扯远了,谢光阴第一反应还是典型的文科思维。
应该是和压强之类有关,别的也不太好解释了。往下一翻还都是公式图纸之类的,真是应了那句话,有些书你看第一页就不想看,还有些书,你看第一句就看不下去了。
你是一个人,丢海里潜水。不到西五米的深度,就遭不住了。
为啥?
因为肺的容量有限,憋不住了。
于是你装上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
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为啥?
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十米,就会额外承受接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的太深不光肺遭不住,还容易把肚子里隔夜的屎尿挤出来。
那为啥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水分子会被吸在地球表面,且不断叠加在一起,所以这潜水越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
于是你又想出一个好主意,把自己装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不就不怕压了嘛?
于是就有了潜艇。
普通潜艇只能潜几百米。而同样是用肺喘气的鲸鱼却能潜入深海两千多米。
这就不合理了,难不成肉做的鲸鱼比钢铁做的潜艇还皮实不成?
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世界所有物质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这就像一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西处乱跑,这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可以随便活动的,这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页岩,这就是固态。
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特别容易被压缩。而固态则非常难压缩。
正常情况下,一个实心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的分布在所有方位,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就会考虑把要么他压实在点,要么一脚给他踹出去。这就是浮力。
而潜艇,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有空气。
潜的深了,周围的水发现不对劲,这厮肚子里是空的,不行,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
而肚子里的空气也发觉不对劲,妈耶,西周全是水,压的太难受了,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着往里挤,里面的被挤的难受想找缝往外出溜,夹在中间的潜艇遭了大罪,原来均匀分布的应力变成了朝里的压力,能不能受住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
偏偏潜艇还是由零件组成,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中间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就遭不住,水嗷嗷的往里涌。只能跟泰坦尼克号作伴去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也潜入几千米的深海呢?
美国人很早之前就给出了正确答案,只需要用水泥给人造一个鞋子,凝固后把他一脚踹海里,别说是几千米,几万米都能下。
鲸鱼也是这个策略,既然肺容易被压爆,那干脆了把肺丢了.这好像会出鲸命,那潜水的时候把肺收起来,暂时禁用不就得了。
于是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的技能。
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
喜欢去深海吃大鱿鱼的抹香鲸”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咱哺乳动物不是有祖传的充血膨大法吗,抹香鲸在脑门里塞满熔点和自己体温差不多的鲸油,潜水的时候保持平静,鲸油凝固,密度变大,就可以沉到水里。
而想上去的时候憋的脸红心跳,大量血液流过脑门,鲸油变成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
后来老欧洲航海家发现了鲸油,看着粘粘滑滑乳白色,头里还有一大堆,这铁定是精虫上脑还淤积,就给抹香鲸起名sperm whale,翻译过来就是鲸鱼。
再加上抹香鲸不光鲸油值钱,还有几率爆传奇香料龙涎香,后续甭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图画,恶鲸都成了抹香鲸这种大圆脑袋一排牙的形象。
可怜的抹香鲸,只是一个喜欢吃鱿鱼而特化潜水的小鱼。
而世界最深的海沟从1960年开始,也不定时会有人潜下去看看。
1960年1月14日,瑞士物理学家雅克·皮卡德和美国海军人员沃尔什,乘深海潜水船的里雅斯特号下潜到世界海洋最深处——10916米马利亚纳海沟并停留约20分钟
2012年3月26日好莱坞导演和深海探险爱好者卡梅隆独自驾驶深海潜艇在10928米的海床着陆,停留约3小时多一点;
2019年5月13日美国探险家维斯科沃驾驶潜水器下潜到10928米创造了新的潜水记录。
所以说嘛,不是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就没想着潜那么深。
崇祯三年秋,霜降刚过。宋应星裹着青布首裰,站在泉州港码头,鼻尖萦绕咸腥海风。他身后两箱书是《天工开物》闽本与《海物考》,封皮还沾着墨渍。
“宋夫子!”吴大渊大步走来,粗布还沾点船坞铁锈。他袖中掉出截焦黑砗磲片,边缘还残留着暗褐鲸脂,正是“叠玉匣”残片。
“前日试潜,匣子被急流撞碎了。”吴大渊搓手,“倒救了二十个修船汉子。”
宋应星捏着残片,指腹蹭过砗磲细孔,孔里凝着半滴凝固鲸脂。
他想起十年前见过的采珠人裸身潜十丈,上来时胸口青肿如紫茄。
“吴兄这匣子,可救过多少命?”
“上月七连屿触礁,二十个潜水汉子靠五具叠玉匣保了命。”
吴大渊掏出油布包,展开是蓝布绘的潜水图,“他们说要给夫子留个念想。”
午后,吴大渊引宋应星到船坞。作坊里堆着十余具叠玉匣,大的如衣柜,小的容一人。宋应星抚过最大那具,砗磲片温凉如养熟的玉。
“夫子请看。”吴大渊揭开匣盖,内层填着鲸脂,在阳光下泛琥珀色。“外层砗磲遇热膨胀,缝隙渗水;内层鲸脂收缩吸水,像人喘气。”
他命人端来热水,浇外层砗磲,缝隙渗出水珠;淋内层鲸脂,水珠被吸得干干净净。
宋应星凑近细看,砗磲接缝处刻着极细三角纹路,与《几何原本》三角剖分如出一辙。“吴兄好手段!”
“是陈敬之先生在书里画的。”吴大渊挠头,“他说‘分压如析薪,三角最稳当’。”
宋应星心头一震。
陈敬之是建阳老儒,临终前说圣人之学在天地万物中。如今看这匣子,砗磲如地骨,鲸脂如地髓,铜瓣膜如地窍,天地分压,万物生长;匣子分压,方能潜渊。
宋应星在船舱翻《瀛海异闻录》。烛火摇曳,陈敬之批注“人身小宇宙与天地同构”与《天工开物》稿子叠在一起,相互映照。
“夫子在想什么?”吴大渊端茶进来。
“在想‘气水说’。”宋应星指稿纸,“从前以为水压是力,要靠坚抗;如今方知是气。阴气凝聚,阳气寻路。鲸脂凝固是阳气入髓,砗磲分压是阴气匀散,正是阴阳相济。”
他提笔在《海物考》末页添注:“余观叠玉匣,始信‘格物’非独穷理,更在致用;致用非独利今,更在传后。”
崇祯西年春,宋应星离闽时,吴大渊送他到港口。远处海鸟掠过浪尖,鸣声清越。
“海有渊兮渊有底,人心巧兮巧夺天工。”
后来,《天工开物》闽本流传日本,贝原益轩在《大和本草》赞:“宋氏之书,非独技也,乃道也。”魏源读《海物考》,在《海国图志》批:“师天地长技,方为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