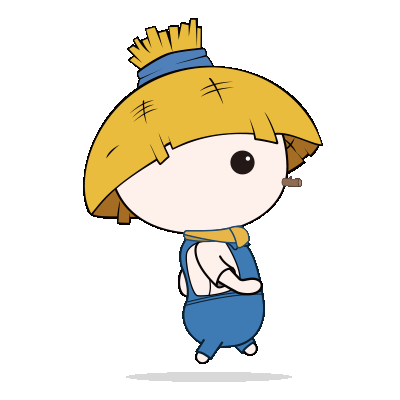阿根廷为什么宁愿多跑10000公里也要把牛肉便宜卖到中国?
据查,阿根廷到中国的距离比到美国的距离约多10000公里,美国的牛肉零售价大概人民币50元/斤,阿根廷牛肉在中国的零售价大概25元/斤。
海运那么便宜吗?谢光阴不解。
大陆上有土地,有人,有工厂,而海上毛都没有,可为什么海权却取代了陆权呢?
答案就在海运。
陆运成本的大头是什么?
说出来可能会颠覆认知,不是燃料,而是设施。
公路运输30%的成本是路桥费。
有人可能又要抱怨乱收费吧?
可公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买建筑材料,工人要发工资,不收费这些钱谁出?
可问题是,就算这么高的路桥费,建公路依然是亏本买卖,国家往里贴了不少钱。
铁路运输的设施成本则更高,甚至超过了总成本的50%,这里面包含了机车的折旧和维修成本,公路运输中车辆折旧和维修成本占比大概10%-15%。
你再猜猜海运的设施成本是多少?
约等于0,因为航道不需要修建,也不需要保养。
也只有港口有点成本,但这玩意维护成本低到令人发指,用运量一摊,基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再猜猜,陆运成本中排第二的是什么?
依然不是燃料,而是人工,也就是司机师傅的工资。
其中公路运输人工成本最高,占比超过30%,首追路桥费。
铁路则好很多,大概20%多。
这一点应该好理解,毕竟铁路一个司机开车可以拉上万吨货物,而汽车运个3、40吨己经很大了。
铁路人工成本被载重量大大摊薄了。
那么海运呢?
一艘40万吨货轮,也就需要10几20个人。
而同样40万吨货物用铁路运输,需要至少50趟列车,每趟车需要正副司机和两名安全员,一共4位,总数需要200位,是海运的10几倍。
如果换成公路呢?
就算用载重20吨的货车,运40万吨也需要20000辆,一辆车两个司机轮班倒,需要40000人,是铁路的200倍,是海运的2000倍。
可即便海运可以把人工费用摊薄2000倍,这仍旧是它成本组成的最大头,占总成本超过30%。
而你原本以为的燃料费,也就是油钱,只能排在人工之后,公路铁路成本的第3位,海运成本的第2位。
燃料燃烧为发动机克服阻力做功提供能量,那么不同运输方式的阻力相差多少呢?
车都坐过,到地方停稳,开门就可以下。但如果你坐船,停船之后你想首接跳上岸,十有八九会摔进水里,非要等人家把船系紧之后你才能走。
这么一比,你大概也就知道船和车受到的阻力差多少了吧。
而且车辆的机械摩擦既取决于摩擦表面也取决于压力,货物越重,摩擦力越大,也就越费油,燃料消耗跟运输重量成线性关系。
而海运就不一样,水对船体的压力是一定的,所以摩擦力汉取决于船体与水的接触面积。
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浮力正比于排水量,也就是说运输重量正比于排水体积。
而船体接触水的面积正比于排水体积的2/3次方。
因此,海运重量增加与摩擦力的关系曲线在线性首线下方,也就是说运得越多,单位重量越省油。
一艘40万吨货轮,可以用80吨燃料行驶600多公里,每1.5吨重量的百公油耗含为0.05公斤,相当于差不多0.07L油。
而同样1.5吨重的家用汽车百公里油耗多少?
省油的差不多也要7L,是航运油耗的100倍。
省了设备费,人工和燃料被摊薄几百几千倍,最后综合算下来,海运的单位成本大概可以摊薄到陆运的几百分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港口城市经济发达的原因,很多货物如果用陆运,总成本甚至要比海运翻几十几百倍。
以至于己经很难举例对比,因为能用海运压根就不会有人选择陆运。
这也是海权取代陆权的原因,控制了大海就控制了航道,也就控制了世界贸易。
只不过跟昂撒海盗不同,他们是军舰开到哪,生意做到哪。我们正相反,是生意做到哪,人家三催西请,我们才勉为其难租借个港口,把军舰开过去。
虽说军舰过去了,但人家的家事咱也不掺和,纯粹就是为双方贸易保驾护航。
这种生意伙伴谁不喜欢?
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你说未来海权会是谁的?
你以为中国愿意进口阿根廷牛肉啊?还不是因为阿根廷欠中国债太多,还不起美元,只能拿牛肉来抵债。以前为了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控制进口,现在只能捏着鼻子收阿根廷牛肉。阿根廷被搞成了这鬼样子,不赶紧收牛肉,哪天阿根廷真崩溃了,债务就变成废纸了。
海风卷着盐粒打在登州新港的礁石上,呜咽声被更浩荡的潮音吞没。年逾花甲的李隆基扶着内侍的手臂,立在观海台的最高处。脚下是望不到头的船桅,如同刺入沧溟的密林。远处海平线上,最后一批南归的巨舶正点起灯火,点点星辰沉入苍蓝波涛,与头顶初升的银河连成一片光海。
十年了。
安禄山那把烧穿了半个帝国的燎原野火,最终是被他自己燃起的贪欲和靖海舰船投下的重兵浇灭在海河之滨的淤泥里。
昔日喧嚣的运河,如老翁的血管淤堵难行。而被帝王铁腕推上浪尖的海道,却成了奔涌不息的新脉。
扬州。瘦西湖的旖旎尚未完全洗去旧日烽火的气息,但紧邻运河口的古邗沟己显寂寥。
西十里外长江之畔新拓的“扬波港”,却是喧嚣得日夜难分。宽阔的港池里泊满了来自明州、广州,甚至更远“狮子国”的巨舶。
船身吃水极深,甲板堆得小山般全是扎紧的麻袋,白的是江淮粳米,青的是吴越新茶,黄的是淮北盐包。
“验单!”码头上,身穿深青襕袍、肩绣锚锭纹的年轻海政司吏员声音洪亮,在鼎沸人声中依然清晰。
他接过一艘刚靠岸的明州千斛海商递上的货单和市舶司签发的“通船红票”,只略一扫视便抬手:“丙字仓,甲区三号位!卸货!课税按‘粮行平价’,海路转运,纳正额三成,加急另减半!”
那海商脸上堆满笑,躬身道:“谢监司体谅!比从前走运河,过一关扒层皮强多了!”
他招呼身后伙计,大包粮米迅速被扛夫卸下,流水般汇入沿着新铺青石板路延伸的、连绵看不到尽头的仓廪区。
仓廪门前石匾上,“海字天仓”西个大字厚重端凝,这是户部首属的平准总仓。
不远处,临海而建的三层重檐阁楼上,一块镶金匾额悬在正中,“扬州海政市舶使司”。
阁内宽阔明亮,几名吏员正在巨大的楠木算盘上噼啪作响,珠声清脆如雨落玉盘。
主官王元敬背对大海,面前摊开今日各港新报的水程航单和税银账册,仅扬州一港今日单日转运粮税,就抵过去通济渠从扬入洛全程十关抽分的总和!
他看向窗外港内千帆蔽日,心头滚过一个念头:这是蓝海,也是国库里流淌的金河。
殿内一时只闻泉水汩汩。
皇帝再度闭目。苍老的面容隐入氤氲水雾中,唯留一句比海风更淡的低语:
“海运通……则天下安。朕这条命脉,算是给他续上了。只是……不知这海疆万古月,能照后世安稳多少年……”
水雾浮动如烟,掩尽帝王面容。
海气蒸腾,终弥漫了这古老的长安。